
8

在平壤购物:朝鲜资本主义世界大冒险
source link: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90221/north-korea-black-market-economy/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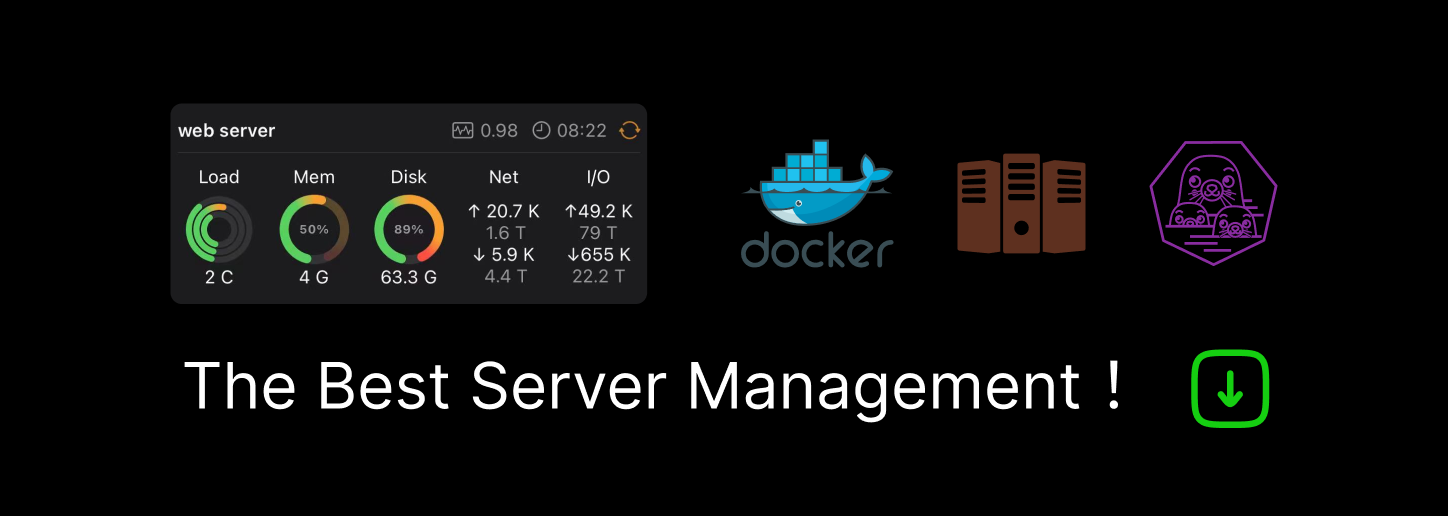
特稿
在平壤购物:朝鲜资本主义世界大冒险
TRAVIS JEPPESEN2019年2月21日
平壤,晚上9点左右。我和我在朝鲜的看管人S的车开进了清流馆空荡荡的停车场,这家餐馆位于宁静的普通江畔。那是2017年的春天,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旅行禁令生效之前最后一批访问朝鲜的美国人之一。那是我五年来第五次访问这个国家,大家都认为美国游客很难去朝鲜,这促使我抓住一切来这里的机会。前三次我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旅行,出奇得容易(尽管会遭到严密的监控和管制);然后是2016年的夏天,我报名参加了金亨稷师范大学(Kim Hyong-jik University of Education)为期一个月的沉浸式朝鲜语课程。现在,我又回到朝鲜,白天另外再上两周的语言班,晚上则悄悄在酒店房间里为我要写的书做进一步的笔记。
这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6岁的S第二次被分配来照看我,已经变得像个朋友了。来到这个国家几次后,我听说年轻的情侣晚上会经常到普通江这一段散步。“我们来这里约会吗?”我开玩笑说。
S笑了。“是的,没错,”她说。“我们今晚和K同志有个约会!”
K(在本文中,我用名字的首字母来指代几个关键人物,以免他们及其亲属遭到报复)是安排我此次访朝行程的国有旅行社的负责人。他曾提议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餐吧喝上一杯,那家店位于平壤东部,不远处就是主体思想塔。蜡烛形状的塔高达170米,樱桃红色的火焰灯彻夜点亮。金正日在1982年下令建造它,作为送给他父亲、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的70岁生日礼物。
在平壤,司机得持有特别许可证才能在晚上11点后在外面逗留,9点出门感觉已经晚了。我们下了车,去欣赏晚春的夜景。除了S和I,还有分派给我们的另一名向导P,以及司机。通常来说,导游的任务是照顾一大群人,但因为负面消息层出不穷——那是朝鲜与西方关系最糟糕的一段时期,新闻里全是试射导弹和监禁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F. Warmbier)(他在朝鲜被监禁17个月期间陷入昏迷,后来死亡)之类的消息——本来就不高的旅游数字更是出现了暴跌。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将是他们负责的唯一外国人。
经过除了我们之外空空荡荡的停车场,我们看到十来个人影在一辆敞开式卡车后侧和河之间穿梭,他们在把似乎是太阳能板的东西卸下,搬到河边,让它们漂浮在平静的水面。我之前已开始注意到市内许多公寓阳台上的太阳能板——对有经济能力的人来说,这是解决电力短缺一种便利的方法——因此也知道,放在水上是一种给它们降温的办法。但是由于数量很多,看上去就像是让这些太阳能板浮在水面作展示,仿佛它们是待售的商品。正当我纳闷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时,P对着她的朝鲜同胞高叫起来:“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我欢快地附和道。陪同的人立即止住了笑,低头看向地面。他们一时间忘了我是个学语言的学生:jangmadang是我不该知道的一个词。
Jangmadang通常翻译成“集市”,是指所谓的“艰苦征程”时期出现的非官方市场,后者是朝鲜政权给整个90年代中后期困扰这个国家的饥荒的正式名称。起初它们是非法市场,朝鲜人赖以获得其月度配给的公共食物分配体系崩溃后,这种市场蓬勃发展起来。在金正日统治后期,政府开始勉强接受它们的存在,并采取措施予以监管:征收摊档租金,控制价格,并对出售的货物加以监控。在金正恩治下,针对民营企业的这类限制措施已经几近取消,jangmadang不再是形成初期的那种促狭的集市摊档,而是大量合法、非法、半合法的市场,售卖各种商品。从近年的脱北者和侨民口中可以了解到,如今在朝鲜,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能买到。但由于政府尚未想出与这种新兴资本主义形式公开和解的方式,和外国人谈论jangmadang被认为是一项禁忌。
这真可惜,因为jangmadang的兴起可以说是朝鲜近些年来意义最重大的里程碑。过去几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来源于此。朝鲜人或许被禁止同外来人谈论这个,但他们不再怯于炫耀自己的消费习惯,任何在近几年目睹过平壤街头展示的人都会认同。对于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半数民众挨饿的国家,万宝龙手表、雷朋太阳镜和巴宝莉时装很难符合对它的刻板印象。尽管极端贫困仍在困扰大量人口,朝鲜社会不再是贫与富的简单画面,而是拥有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多个社会经济阶层。日益壮大的上中产阶级在平壤最显而易见,但其它地区也出现了暴发户阶层,如港口城市清津以及和中国接壤的许多地方,那里合法和非法贸易在继续繁荣发展。
我在和向导们的尴尬沉默中煎熬着,努力想要重新开始谈话,但想不出从太阳能板这个话题能引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一个人影渐渐朝停车场走来,使我得以摆脱独自挣扎。那是个37岁的男子,身穿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法兰绒衬衫,脚蹬荧光色耐克鞋。若不是胸前郑重地别着印有金日成和金正日笑脸的胸章——朝鲜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在公共场合佩戴这种胸章——我意识到,他很容易会被当成一名韩国同胞。
广告
“K同志来了,”S叹着气宣布道。“终于。”
艰苦征程的成因有很多,但很可能主要原因在于1991年苏联的垮台。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中,苏联给朝鲜提供了用以维继政权的援助,如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出售石油,换取做工粗糙的朝鲜产品。对俄罗斯联邦而言,与朝鲜继续这种贸易援助在政治上毫无道理,更不用说在商业上。根据一项估计,1990年至1994年间,朝鲜和俄罗斯的年度贸易额从25.6亿美元骤降至1.4亿美元。之后数年中,洪水导致危机恶化,朝鲜经历了灾难性的饥荒,60万至100多万人因此丧命。
由于粮食短缺,政府无法通过配给计划提供粮食,朝鲜人开始放弃官方的中央计划经济。全国各地的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销售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食品、香烟、日用品到非法外国出版物应有尽有。根据丹尼尔·图德(Daniel Tudor)和詹姆斯·皮尔逊(James Pearson)的著作《朝鲜机密》(North Korea Confidential),这些摊点通常是由中年已婚女性经营的,她们令人不安地“使国家卷入了市场化”,被迫向当地的党干部缴纳“摊点税”。2009年,在金正日治下,政府实施了一场灾难性的货币改革,试图关闭市场,并禁止国内市场活动。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不满,一名劳动党高级官员被当作政府决策的替罪羊处决。尽管如此,朝鲜政权未能兑现喂饱国民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jangmadang提供的灰色市场填补了这一空白。
如今,朝鲜有400多个被批准的市场,拥有大约60万家商贩。货币改革令许多商人失去了财富和积蓄,此后交易的首选货币变成了美元和人民币。根据一项调查,大约90%的家庭支出都是在这些市场;它们实在太普遍了,以至于人们造出了“集市一代”这个词,他们从小就知道有它的存在。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市场活动得到容忍;而且正如我在访问该国时亲眼目睹的那样,它们已经慢慢地进入了官方行业。
在密切观察朝鲜的人士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韩国经济学家金炳连(Byung-Yeon Kim)在2017年出版的《揭开朝鲜经济面纱》(Unveiling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一书中,率先提供了有关这种转变的确凿数据。金炳连说,朝鲜非正式经济中,普通工人的收入是拥有正式工作工人的80倍。在国有企业中,大约有23%的员工同时从事一些非正式的工作。在朝鲜所有的企业中,至少有58%的企业雇佣所谓的“8/3工人”,他们为了不去上班并参与非官方的市场活动而向企业支付一定费用;这些资金对这些企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收入形式,帮助它们继续支付正式员工的工资。这种程度的系统性腐败代价高昂:从1996年到2007年,人们用于贿赂的支出估计占家庭总支出的5.2%至10.7%。尽管存在普遍的腐败,据一些人估计,在最新一轮制裁于2017年秋季生效之前,朝鲜经济的年增长率超过4%。“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金炳连写道。
但这种转变很难与该国自诩为社会主义天堂的形象调和起来,朝鲜一直在向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人民展示这种形象。韩国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硕士研究生彼得·沃德(Peter Ward)的研究重点是朝鲜经济,去年夏天在朝鲜旅行了将近一个月,研究政府出版物和学术期刊。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该国颁布了新的规定,解除了对“订单合同”使用的限制,只要它符合国家的目标即可。沃德在他最近的播客中解释说,订单合同涉及国有企业与客户协商制定价格。换句话说,它们是一种市场力量,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他解释说,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相反,在经济的几乎每个部门,供求经济学都在被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运用着。
每个朝鲜公民一出生都会被分配到一个被称为“出身成分”(songbun)的分类,它对本人是保密的。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主要的类别——忠诚、动摇和敌对——还有51个子类别作为限定。这个分类是决定公民一生际遇的主要因素。它和家族出身有关,基于一个人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建国期间——甚至更早——所做的事情。
那些在1945年朝鲜解放前与金日成在游击战中并肩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人,被赋予了最高级的出身;他们的许多后裔如今占据着政府最高层职位。那些被打上“敌对”标签的人可能是前地主的后代,可能是与日本殖民者合作的人的后代,也可能是在韩国有亲戚的人或基督徒的后代;他们大多被派往朝鲜不适宜居住的山区,被禁止进入平壤或其他大城市,被迫以农民或体力劳动者的身份勉强度日,几乎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即使大多数朝鲜人不能明确知晓,凭着自己的居住地、祖先是做什么的、从通常自上学期间就开始得到的机会和遭到的歧视,通常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出身成分是什么。出身成分显然是警察国家机构的一个明确组成部分,历史上一直和朝鲜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有证据表明,随着朝鲜进一步走向自由市场,这种政治阶级制度也在受到侵蚀。
在2017年上一次访问朝鲜之前,我在首尔花了3个月时间采访脱北者。其中一位是2006年离开朝鲜、现年30岁的金范希(Bomhee Kim,音)。她的童年恰逢饥荒年代,在那段时间里,她亲眼目睹了出身成分制度是如何开始像这个国家一样分崩离析。她告诉我,一切都始于1994年7月8日金日成的去世——好像伴随着伟大领袖的去世,不可避免地总会有大规模灾难。对当时只有五岁的金范希来说,这完全说得通。人们在全国各地的领袖塑像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纷纷落下眼泪。好像神也为之动容一样,天降倾盆大雨,毁坏了那年的庄稼收成。
到1997年,国家规定的对金日成的三年悼念期结束的时候,在他的儿子和接班人金正日的领导下,宣传口径转向了奋斗与忍耐的信息。朝鲜的工资一直很低,低到几乎没有意义的程度;所有的必需品,包括食物,原本都应该由国家的公共配给系统提供。随着俄罗斯撤走援助,配给很快就耗尽了。“父母告诉我,有一天,我们不再得到政府发的食物,”金范希回忆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得不靠自己奋斗了。”
金范希记得,她渐渐习惯了家乡的地上和附近的山里躺着死人的景象,人们会到山里去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包括老鼠和树皮。公共分配制度崩溃后,饥饿的民众别无选择,只能违反宪法,开始自己做生意。
由于通往韩国的路被地雷密布的非军事区阻断,数不清的朝鲜人越过边境逃往中国。中朝边境也成了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生存途径,各种贩子经常带着食物、商品和现金,以及像DVD这样的更非法的商品,在边境上往返,实际上让朝鲜人接触到了更广阔、更富有的世界。金范希家里的地方离一座金矿很近,这时的朝鲜已经足够腐败,所以如果你认识合适的人,就能从矿工那里直接买到金矿。她的父母以黑市价格搞到了未提炼的金子,在家里进行提炼后,以官方价格将纯金卖给边境那边的中国投资者,获得了利润。她的父亲后来干脆用钱贿赂领导,不再去上班——随着经济的崩溃,所有的行业都陷入了停顿,所以上班也没什么可做的。

与此同时,金范希的母亲开始在jangmadang出售自制的食品。从朝鲜偷带出来的视频揭示了这些早期市场的样子,它们是在大城市泥泞的边缘地带或隐蔽小巷里的原始集市,商人们把商品摆在地上铺的油布上、或装在普通的袋子里,自己则蹲在或站在货摊旁,如果有官员过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商品兜起来跑走。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要么死了,要么抛弃了他们)自发形成了狄更斯小说里那样的帮派。他们会在集市上四处游荡,从购物者的背包里偷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分散小贩的注意力,以协助同伴们偷摊上的食物。他们经常遭到毒打,甚至在与敌对帮派的战斗中被打死。还有一些孤身一人的孩子,有的只有两三岁,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从成堆的动物粪便中拣出未消化的玉米粒,当场吃下。金范希11岁的时候会在放学后骑自行车去批发市场,用1000朝鲜元(按如今的非官方但普遍采用的汇率,约合12美分)买100块糖,然后跟母亲一起在偏远农村地区的jangmadang上把糖果卖掉,赚取10%的利润。
朝鲜的社会主义再也没有从这种市场经济的入侵中恢复过来。虽然出身成分从未消失——特别糟糕的出身仍是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一大障碍——但现在,人们可以想办法绕开它。与我交谈过的另一位年轻脱北者能够得到在平壤居住所必须的许可证,当然不是因为她父母的出身成分——他们的成分不坏,但也不太好——而是靠他们的钱和商业关系买来的。这位脱北者要求我隐去她的名字。她在中国边境上的一座城市长大。在整个21世纪的头10年里,边界的管理比今天更松散,这种市场非常繁荣。这名脱北者会弹钢琴,曾梦想在首都学习音乐。虽然她母亲的生意做得很好,但还是支付不起相当于1万美元的贿赂,让女儿进入朝鲜最好的音乐学院。所以她做出了次好选择,与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直接谈妥。这位教授早就不再去上班,而是开始私下教授精英家庭的孩子。每月支付了食宿费和学费后,她可以住在教授家的一个空余房间里,在平壤学习钢琴。
据金炳连在近期的脱北者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政府雇员的平均月工资略低于2200朝鲜元,约合26美分;而在jangmadang工作的人平均月收入为172750朝鲜元,约合21美元。(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数字,平壤目前的大米价格是每公斤4200朝鲜元,约合51美分。)虽然历史上的情况是,脱北者从韩国给他们仍生活在朝鲜的穷亲戚们寄钱——这个情况类似于生活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我已从几名脱北者那里听到了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富有朝鲜人每个月给他们在韩国读书的脱北子女寄几千美元。这些人属于中上阶层和上层,他们不只是在jangmadang卖东西,还在纺织和海鲜等行业用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价格从事贸易。
如今,在国有企业担任管理职务的个人几乎可以从事任何他或她想做的盈利活动。这些活动都能得到政府部委官员的“批准”,这些官员本质上是一种拿回扣的商业伙伴,他们然后再给自己的上级送回扣,这种做法一直延伸到统治家族及其伙伴。一些报道朝鲜的记者把朝鲜政权比作收取保护费的黑手党。
当我们的车越过宽阔的大同江上的大桥进入东平壤时,路口的红灯让我们停了下来,前面可以看到一座有弧线屋顶的长长的建筑。“那是柳京健康中心,对吗?”我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K同志。
“是的,是的,”他点头答道。
“街对面的那个呢?”我指着一幢有闪亮的蓝色反光立面的新建筑问道。“那也是柳京吗?还是它有别的名字?”
K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你去过那里?”他不相信地问道。那不是他的公司经营的旅游线路上的正常一站。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可以进到那里。
我的确去过那里,那是在过去的一次由K同志的竞争对手安排的访问中。新健身俱乐部的设施令人印象深刻。一层的一个商店出售各种奢侈品:定制西装、丝绸领带、精美的皮夹、闪闪发光的劳力士手表。一个零食店出售各种各样的进口软饮,包括越南包装的可口可乐系列产品。与某些评论人士散布的观念相反,这些不是只为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而摆样子的地方,那天在男更衣室里的20几名顾客,看上去真的被我和选择与我一起来享用这些设施的同团另外一名外国男子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这些设施包括传统的朝鲜桑拿汗蒸幕,其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我在首尔偶然光顾过的地方,里面还有一个带有人工瀑布的室内游泳池。
K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是……柳京健康中心的附属。”他的用词小心翼翼。“但这里带斜面屋顶和室内溜冰场的主楼……你也到过那里吗?那是给普通人用的。”
最近两次访问期间,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听到“普通人”这个词。它通常带有一丝贬义,显然是指下层阶级:工薪穷人,农民和劳工,那些没有幸运地受雇于某个被认为可获利且有地位的场所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就得以进入街对面那样的地方;它也指那些缺乏精明头脑和关系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会在jangmadang的灰色市场世界或者国有企业管理高层中出人头地。
我们的车开进了停车场。一间卖进口处方药的商店和另一间服装、家具和家居用品综合商店之间的一道楼梯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K同志最爱的餐吧大同江啤酒吧(Taedonggang Beer Bar)。里面全是木、铜、镀铬的华丽装饰,雅致的昏暗灯光,身着礼服的调酒师。若非平板电视上正播放着牡丹峰乐团(Moranbong Band)的演唱会,而不是球类游戏,我可能已经在想象自己身处芝加哥或波士顿某处的高档体育酒吧了。
店里客人不少,包括朝鲜的雅皮士,经过一天疲惫的工作后,他们松开了领带和中山装衣领。有一种当地说法形容这些人:dongju,即金主。这些人无疑不是“普通”人,虽然他们也代表着平壤民众中日益壮大的一个比权贵低一级的群体:新富阶层。他们不大会去市场看摊,而是从摊位收租,并在名义上受雇于官方部门的同时,参与jangmadang的其它经济活动:从负责运送中国走私货物的物流,到经营商店和企业,从这类货品的销售中获利。
我的看守人们和我选了张桌子坐下,K同志则去吧台点了几份啤酒和一份泡菜煎饼。S虽然名义上仍是导游,但最近升到了管理岗位。我问她没旅行团的时候她一天都在干嘛,最近基本上都没什么旅行团。
她害羞地笑了笑,说:“噢,坐着,想想打发时间的新点子。办公室的一些男同事《魔兽世界》已经打得很娴熟了。”
像我见到过的大多数朝鲜人一样,她不想过多谈论她工作时一整天都干了什么,但根据我之前访问朝鲜时她无意中吐露的内容,以及她无休止地响起的智能手机,我已经拼出了一幅朦胧的画面。S的家庭远非普通人家。她所称的做“商人”的父亲曾在海外某朝鲜大使馆待过多年(K同志也是)。她和父亲都会时不时出国到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旅行(K同志也是)。她做厨师的母亲经营着自己的餐厅,特色是欧洲和美国菜,并提供外烩服务。
有一次,S直白地问我在目前生活的德国是否有认识的生意人,这人要有比较大胆的作风,不太在意违反制裁。我问她感兴趣的是哪类业务。她不假思索地提到了法国化妆品、IT服务(她告诉我她的兄弟是个天才程序员)、用于制作假发的人发。“什么都行,真的,”她说。
在金正恩2011年继承权力之后,其政府的核心是所谓的“并进”政策:经济和军事(如核武器)同步发展。这在很多方面是他父亲军事第一政策的继续,该政策不仅扩大了朝鲜常备军的规模,还让军方要员掌握了前所未有的重权。但在2018年4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金正恩宣布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并进”政策正式结束。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已经完成,并取得了“胜利”。
虽然外界一直在争论,金正恩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弃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春季宣布消息之后,军方高层出现了人员调整,可能表明金正恩的决定在军方导致了某种不和谐,军事机关也普遍出现降级。金正恩继续宣布,向前迈进的唯一关注点将是发展经济,同时启动外交程序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除在新加坡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简短会晤外,金正恩迄今已和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进行过三次长时间的会谈。文在寅曾反复表示,他相信金正恩的意图是真诚的。
众所周知,想弄清朝鲜政权的目的是什么会很困难,但在经济自由化与外交政策转变之间,乐观的解读是,金正恩想要开放朝鲜。曾撰写过多部朝鲜现代史专著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对这一问题尤为乐观。“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相信,金正恩正朝着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选择的方向迈进,”他对我说。“我认为他的理想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使朝鲜可以用中国和越南的方式,对世界经济开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月以来与韩国和美国的外交动态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实际上过去25年来,这一直是朝鲜的目标,但他们发现很难明说出来:在苏联解体后,以某种方式让美国来解决它的战略性问题。”为让经济实现有意义的增长,朝鲜将需要美国和联合国取消经济制裁,允许朝鲜获得商品以及尤为关键的资金。但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许多人对金正恩的举动深表怀疑,鹰派朝鲜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要糊弄美国,让它取消制裁,自己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
问题仍然在于,铁板一块的朝鲜政治体系能否经受住市场经济带来的破坏力量。这个等式的关键可能是“金主”这些人已经让自己成为一个复杂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鉴于朝鲜公布的可靠数据很少,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人属于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阶层。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正如金正恩已经开始依赖金主,金主也依赖于金正恩政权的生存。生于俄罗斯、在朝鲜读过书的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认为,在苏联的垮台过程中,中产阶级对体制的不满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不同的是,金主担心朝鲜政府的崩溃,以及随后同朝鲜半岛的统一,那将意味着朝鲜不得不与韩国这个全球经济巨头竞争,让朝鲜人处于次一等地位或者更糟。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周围的贫穷——以及他们中许多人是从“普通人”起家的事实——因此认为,维持现状符合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金主很难被认为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阶层;他们只是想让政府不要管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发财了。
喝了一轮啤酒后,K同志告罪说他不得不提前结束此次聚会。因为他第二天早上要去南浦出差。在我们起身离开之前,他送给我一件礼物:一个昂贵的打火机,上面印着千里马的图案,千里马是亚洲神话中的一种长翅膀的马,以惊人的飞行速度著称。它令人想起金日成在1950年代末提出的千里马运动,那是一场类似于中国的大跃进和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te Movement)的大规模劳工运动,旨在通过“思想激励”来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给超额完成任务的人授予千里马骑手的头衔。此外,政府还鼓励员工少喝汤,以减少上厕所的时间。千里马运动被誉为朝鲜历史的里程碑,但一些外部观察人士声称,它所带来的不过是疲惫、营养不良的朝鲜民众和一系列粗糙、劣质产品,只是昔日政府经济措施失当的又一个例子。
K还递给我一盒绿色的香烟。“这是平壤的新潮品牌,”他笑着说,然后压低了声音:“精英就抽这个。”我大声念出生产它的公司名称:“Naegohyang”。我的家乡。
在收银台前,我打算买单,但K同志挥了挥手,从他的杜嘉班纳衬衫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50美元钞票,抽出一张拍在桌上。女服务员的手指在袖珍计算器上舞动,而后找钱给他,其中有美元,还有几千块印着金日成笑脸的朝鲜元。K同志满脸怒容地把美元装进口袋,把朝鲜元推回给女服务员,我们慢悠悠地走到停车场,司机正在那里等着。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