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文字打败时间 » 2008 » 9月
source link: http://www.fengtang.com/blog/?m=200809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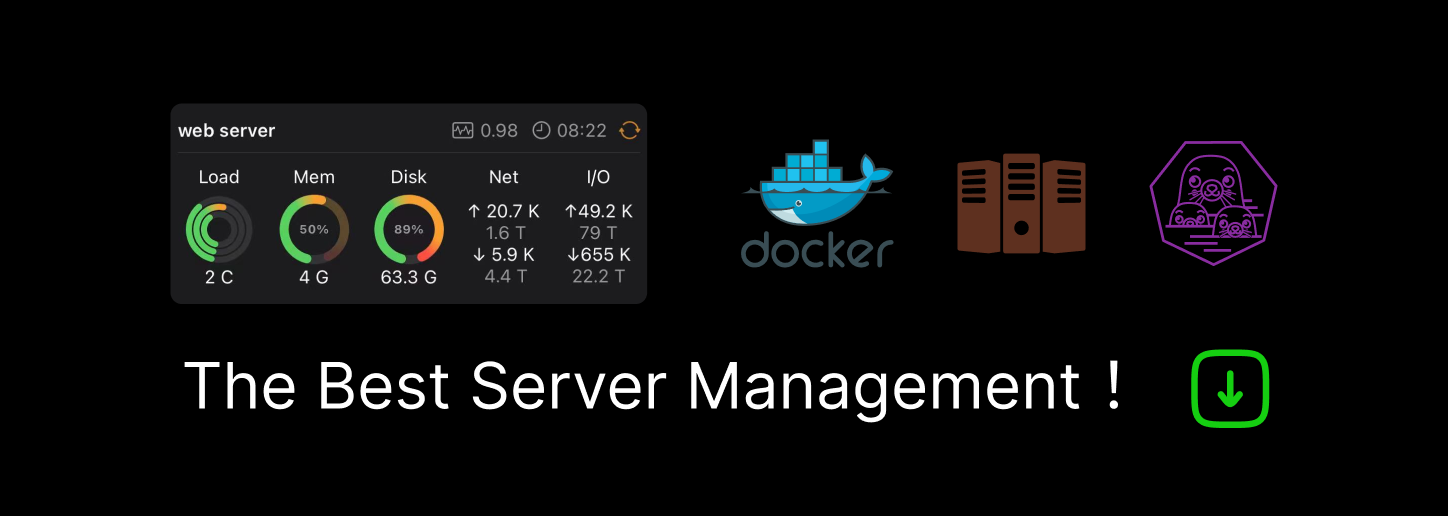
2008-9-14 03:33 下午
三十年河东:乔厂长上任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改革开放正式开始。二十九年前,一九七九年,天津三十八岁的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二十九年后,二零零八年,乔光朴如果还活着,应该八十五了。
伟大文字的主要特点就是能打败时间和空间。一千年一转眼,“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还是像弯刀一样戳心,让你抬头看到弯刀一样的月亮。一万里一闪念,“照亮我生命的光,点燃我情欲的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还是像巴掌一样扇你,让你觉得A股跌到两千点算个屁。
由于蒋子龙的功力,乔厂长上任近半个甲子之后,他面对的一切依旧鲜活而真实。
国有企业体制依旧,所有者缺位依旧。属于全体人民,就近似于谁也不属于。向党负责,就近似于向主管领导负责。领导交办、集体决策,做企业就近似于做官。乔厂长在上面没有政治根基,对下属不懂恩威并用的权术,于周围相关利益方不解“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风情,如果他的顶头上司机电工业局局长霍大道是霍小道或者霍无道或者霍邪道,他第一次去澳门葡京,接他的检察官就能挤满蛇口或者福永客运码头,他第一次去洗头房,接他的警车就能停满一条街,第一辆警车的副驾驶位置上一定坐着他的老婆童贞。
国有企业还是远离市场。当时的乔厂长最大的梦想是把电机厂的产量数字搞到二百万千瓦,在五十六岁的年纪,用小伙子般的热情抱住童贞的双肩:“喂,工程师同志,你以前在我耳边说个没完的那些计划,什么先搞六十万千瓦的,再搞一百万的、一百五十万的,制造国家第一台百万千瓦原子能发电站的设备,我们一定要揽过来,你都忘了?”现在看各省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文件,满眼还是“我们是国内最大的1.5兆瓦级风电机组的研制基地,今年将研制3兆瓦风电机组”。问起销售额还是充满骄傲,“接近四十个亿”,问起净利润还是莫名其妙,“三百万不到吧,我也不知道怎么整的”。
国有企业机制依旧,业绩无法衡量依旧,绝大多数的时候,做事的性价比远远小于不做事。“大多数还不是紧跟党的中心工作,这个运动跟得紧,下个运动就成了牺牲品。照这样看来还是滑头好,什么不干最安全。”乔厂长们还是这样分配精力的:“百分之四十用在厂内正事上,百分之五十用去应付扯皮,百分之十应付挨骂、挨批。”最后的希望还是:优秀的国有企业一把手,一个人提刀而立,他的血总是热乎乎的。
由于蒋子龙的功力,半甲子前创作乔厂长使用的手法在现在的影视中还在被广泛应用。
语言筋道。“他像脚后跟一样可靠”,“我只有半个舌……舌头,而且剩下的这半个如果牙齿够得着也想把它咬下去。”
人物鲜明。“有一张脸渐渐吸引住霍大道的目光。这是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扩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眼;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阔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如果他脑门儿上刻着两个字,一定是“好人”两个字,这样的人不可能变坏,即使变坏,也是多名女特务利用多种方式花了好长时间害的。仿佛如今,宋丹丹演绎纯情戏一定会笑场,柳云龙演嫖娼犯一定是为了我党提取特殊变种的艾滋病毒毒株而舍身忘死。
矛盾重重。“(年轻而有污点的副厂长郗望北)这样谈话太尖锐了,简直就是吃饭前那场谈话的继续。老的埋怨乔光朴袒护新的,新的又把乔光朴当老的来攻”,下岗愤怒青工杜兵“三天没上班,和市里那批静坐示威的人可能挂上钩了。今天下午,他回厂和几个人嘀咕了一阵子,写了几张大字报,说是要贴到市委去,还要到市委门口去绝食。”狡猾奸诈的原厂长冀申“相信生活不是凭命运,也不是赶机会,而是需要智慧和斗争的无情逻辑!因此他要采取大会战孤注一掷。大会战一搞起来热热闹闹,总会见点效果,生产一回升,他借台阶就可以离开电机厂。同时在他交印之前把郗望北拿下去,在郗望北和乔光朴这一对老冤家、新仇人之间埋下一根引信,将来他不愁没有戏看”。
二十九年前,一九七九年,快到元旦了,在王府井靠长安街一边的路口,北风吹,红旗飘,斜阳在紫禁城的屋檐上摇。我刚在东风市场一楼吞完两个猪肉大葱包子,猪油在双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凝结成细白的面条。我老妈刚烫了个大黑卷花头,第一次看到“可口可乐”这个不西不中的名字,她喜欢招牌上的大红色,“喜庆”,给我买了一瓶。渴了,我用塑料麦管狂吸一口,气泡和药汁儿猛地从胃里沿着食管里反上来,我一口吐在地上,骂,“妈,妈屄的,这么难喝的东西还敢卖四毛钱啊?”
上一篇:断绝
下一篇:读齐白石的二十一次唏嘘(5、6)
2008-9-12 09:50 上午
断绝

你执墨玉刀在黄白的腿骨上刻一个“鸟”字
腿骨生出肌肉长出翅膀飞入蓬蓬的柞树林子
入诸淫舍
入诸淫舍
入诸淫舍
入诸酒肆
入诸酒肆
入诸酒肆
入诸僧房
入诸僧房
入诸僧房
前念前念
前念前念
前念前念
今念今念
今念今念
今念今念
后念后念
后念后念
后念后念
你用白玉掌在身体里掏出一只飞鸟
你黑长的头发拂到飞鸟黑长的羽毛
上一篇:球
下一篇:三十年河东:乔厂长上任三十年了
球
冯唐,比目鱼

许多年以后,面对马戏团老板被踩成肉饼的尸体,七喜准会想起,他七十七岁父亲带他去见识南天萤火虫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马戏团老板是个除了鸡鸡不硬到处都硬的人,特别是心。即使看到镇子上几百人凑到他的马戏蓬,马戏团老板心还是没有甜蜜到柔软,还是在想,为什么不是一千人,“一千人就是一千个银元而不是几百个银元,就是四位数的财富而不是三位数的财富。”
“我有会用大拇指走路的大象,会用舌头打架的肉球,会让你笑死不偿命的小丑,前面长得像章子怡后面长得像司马懿的斑马。这么多好东西,怎么只有几百人看?”马戏团老板骂。
观众全部到齐了,在露天的大蓬里谈笑、吵闹、吃、吐、张望、思考人生。
“大象赶快出来!”观众喊。
“肉球赶快出来!”观众喊。
“小丑赶快出来!”观众喊。
“司马懿赶快出来!”观众喊。
马戏团老板骂:“大象,赶快用你的拇指走出去!”
大象白了马戏团老板一大象眼,很大很白,然后一动不动。马戏团老板骂了三遍,大象还是不动,前台观众的叫喊声更大了。马戏团老板找到肉球。
肉球是个没手没脚的老人,他的名字叫七喜。肉球七喜今年五十七岁了,已经给这个马戏团干了五十年。五十年前,现在的马戏团老板还是个小孩儿,但是那时候他的鸡鸡就已经不硬,心已经铁硬了。五十年前,马戏团老板逼着他爹马戏团老老板买下肉球七喜,“爹,你傻啊,买个死的皮球还比这个活着的肉球贵呢。”
马戏团老板找肉球七喜,是因为他听得懂禽兽的语言。其实,肉球七喜还能说禽兽语言,他有个巨大的舌头,发出正常人无法发出的频率。
“大象说,它病了,他的脚受伤了,他的左脚或者右脚或者左腿或者右腿长了个鸡眼,否则他能跑一百一十米栏。”肉球七喜翻译道。
“不行,舞台上,全宇宙亿万人民都看着它呢,它必须跑。我们马戏团的崛起就靠它了,它必须跑。哪怕挣扎着转一圈,哪怕之后断了腿,哪怕以后再也不能走路,今晚也要跑!”
“大象说,它就是不跑。”
前台已经传来震天的漫骂声和跺脚声,兴奋比愤怒多。
“肉球,你先滚上前台去。我来收拾大象。”
肉球七喜来到前台,在灯光照耀下表演他长期熟悉的花活。他的舌头长而灵活,舌头扑蝴蝶,舌头击鼓,舌头拉车。坐在前排的小女孩说:“好恶心啊,口水流了一地,我都闻得见!”
肉球七喜回到后台,马戏团老板已经被发了狂的大象踩成了肉饼,软软地摊了一地。
大象站在后台,说:“我就是不跑,打死你也不跑。”
夜很深了,所有人和禽兽都散了,只有肉球七喜、小丑和病了的大象还在,不知道去哪里。
大象说:“我天生是孤儿,没有地方去。”
小丑说:“我天生不是孤儿,但是我能讲笑话的第一天,就把我爸妈逗得笑死了,就成了孤儿,我也没有地方去。”
肉球七喜说:“我父亲七十岁那年生下我,他一生娶了七个老婆,某个岁数之前,他最大的乐趣和白雪公主一样,就是一晚上睡七人,某个岁数之后,他最大痛苦和白雪公主一样,就是一晚上睡七人。我生下来就没手没脚,我父亲养了我七年,每天给我喝花生猪手汤,以为我会长出手脚来,但是七年之后,我还是一个肉球。在我七岁生日过后的第一天,他把我卖给了马戏团。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我父亲也该不在人世了。”
大象说:“那你也没有地方去啊?”
肉球七喜说:“其实,我有个地方要去,我要去南天黄金海岸。我七岁生日那天,我叔叔从遥远的南方回来,我七十七岁的父亲带我去看他。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所有的星星都灭了,我在我叔叔的行李夹缝里见到一个像毛毛虫的萤火虫,她说她叫南天萤火虫。她说,这是真的,南天萤火虫和北方的萤火虫不一样,不像蝴蝶或者飞虫,不像坐在花瓣顺流而下的拇指姑娘,而像蚕或者淫虫。南山萤火虫说,如果我帮她逃进屋后的山林,她就是给我一件宝物。”
小丑说:“后来呢?”
肉球七喜说:“后来,我看到她也没手也没脚,就帮她逃进黑暗的山林。她说,那个给我的宝物是盒火柴,在我叔叔的行李里。那盒火柴写着著名商标: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火柴。点燃那盒火柴里任何一根火柴,就有一个精灵出现,满足我一个具体的愿望。”
小丑问:“什么叫具体的愿望?”
肉球七喜说:“就是一个具体的愿望。不能是二屄类或者傻屄类的脑筋急转弯,比如,我的愿望就是满足我所有愿望。不能是违反自然法和道德律的愿望,比如,我的愿望就是长生不老。南天萤火虫说,精灵智商都低,只能求他们做非常具体的事情,不能让他们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比如,不能说,你让我满足吧,而要说,你去变出一锅红烧肉吧。”
大象说:“后来呢?”
肉球七喜说:“临分手,南天萤火虫告诉我,在她生活的南天,在海的边缘,有片巨大的榕树林,其中一个榕树下面,有个姓路的医生。路医生本领很大,治很多怪病,让哑巴说话,让和尚打架,让灰姑娘写长篇小说成为美女作家。你如果找到他,或许他能治好你的病,让你长出手脚,或许还能让你用新长出来的手拿起笔来写作呢。”
小丑和大象说:“这听上去像个童话故事。”
肉球七喜说:“我七岁那年,也是这么想的,直到如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没有地方去了,我也这么大岁数了,我想,去趟南天。”
小丑说:“也是,闲着也是闲着,或者闹场革命,或者去个最遥远的远方,我陪你去吧。”
大象说:“全宇宙人民都怀疑我了,我也觉得没意思了,我驮你们去吧。”
于是小丑把肉球七喜拽上大象,大象背朝北斗星的方向,开始南天的旅途。
走了七天七夜,遇上一座大山。大山大得一望无际,一座山就是一个世界。
大象说:“我驮不了你们过大山了。我老了,如果我还年轻,如果二十年前,咱们打死马戏团老板,跑出来,我一定能够驮你们过这座大山。”
肉球七喜说:“是该试试‘卖火柴的小女孩’牌火柴的时候了,看看是否真的有精灵出现。”
肉球七喜用舌头从他身体上最隐秘最深沉的肉缝里拿出一包火柴,磷片竟然还是干燥的。肉球七喜颤抖地打开,取出一根,火药头朝下,磨擦磷片,没着。再取出一根,再擦,没着。
肉球七喜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或许火柴已经被我的汗水浸湿了。如果五十年前我就试,或许会好很多。”
肉球七喜一根根试下去,几乎用光了半包,他几乎失去信心,突然,一根火柴被点亮了。
一只巨大的鹏从南边的天空飞来,大得无边无际,不知道翅膀有几千里长,“过了这么多年,谁找我?”
肉球七喜说:“南天萤火虫说,你能帮助我,我们要飞越那高山,我们要去南天黄金海岸。”
大鹏说:“没有问题。但是我已经老了,我不能负重了,我只能驮你和小丑了。如果是五十年前,我可以驮着大地去见老天。”
大象说:“你们走好吧,我离开了马戏团,见到了大山,我已经很高兴了。肉球,如果你长出了手脚,甚者变成了作家,你要记得写到我。”
飞了七天七夜,遇上大海。大海大得一望无际,一海就是一个世界。
大鹏说:“肉球和小丑啊,恐怕我不能带你们去南天黄金海岸了。我是一只很老很老的鹏了,我已经飞了七天七夜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如果是五十年前,我一定把你们送到目的地,但是现在不行了。”
肉球七喜说:“没关系,已经很感谢你了。”
大鹏飞走。肉球七喜继续划他剩下的火柴,一根,没着,再一根,没着。“我真希望我五十年前划这些火柴啊。”
突然,又有一根火柴亮了。
一只巨大的鲲从海面浮出,大得无边无际,不知道脊背有几千里高,“过了这么多年,谁找我?”
肉球七喜说:“南天萤火虫说,你能帮助我,我们要穿越这大海,我们要去南天黄金海岸。”
大鲲说:“没有问题。但是我已经老了,我不能负重了,我只能带你,但是带不动这个小丑了。我都没有弹性了,塞不下什么东西了。如果是五十年前,我可以吸干南海去灭地狱之火。”
小丑说:“你们走好吧,我离开了马戏团,见到了大山和大海,我已经很高兴了。肉球,如果你长出了手脚,甚者变成了作家,你要记得写到我。”
游了七天七夜,遇到海岸。海岸大得一望无际,海岸边无数的一模一样的榕树,一个海岸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榕树就是一个世界。
大鹏说:“肉球啊,这里已经是南天黄金海岸了,恐怕我不能带你找到路医生了。我是一只很老很老的鲲了,我已经游了七天七夜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如果是五十年前,我侧耳倾听,一定判定路医生的方位,但是现在不行了,我已经聋了。”
肉球七喜说:“没关系,已经很感谢你了。”
大鲲游去。肉球七喜继续划他剩下的火柴,一根,没着,再一根,没着,只剩最后一根火柴了。
“我真希望我五十年前划这些火柴啊。”
突然,最后这一根火柴亮了。
一只巨大的白虎从榕树林中窜出,比马戏团的大象还大,“过了这么多年,谁找我?”
肉球七喜说:“南天萤火虫说,你能帮助我,我们要找到能治各种怪病的路医生。”
白虎说:“路医生的榕树距离这里很远,我已经老了,我跑不动了。如果是五十年前,我可以窜进榕树林,把路医生叼来见你。但是你不要担心,我还有一口丹田气,我大吼一声,或许路医生会欢天喜地地跑到咱们面前来。”
肉球七喜说:“我已经用尽我的火柴了,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你试试吧。”
白虎向着榕树林大吼一声:“路医生,有北方的投资者来了!来了!了!”头顶上的云彩在这一瞬间被吹走,脚下的沙坑在这一瞬间下陷。
肉球七喜用舌头勾住白虎的尾巴,从沙坑中艰难地爬出来,路医生已经欢天喜地地站在坑口了。
“我是路医生的儿子,所以也是路医生,谁找路医生?”
肉球七喜说:“五十年前,南天萤火虫告诉我,在她生活的南天,在榕树下面,有个能治各种怪病的路医生,能治好我的病,让我长出手脚。”
路医生说:“如果你五十年前来,我爸爸老路医生正当壮年,一定没有问题,他一定能让你长出手脚,还能让你用新长出来的手拿起笔来写青春美文,还能让你用新长出来的脚踩油门成为竞赛车手。现在老路医生已经不能行医了,他的手术都要我来做了。”
肉球七喜说:“你做也好。南天萤火虫说,路医生就好。”
路医生说:“好,你先在这个手术同意书上签个字吧。”
手术同意书是这样写着:“由于目前医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尚难杜绝手术病人在术中和术后可能发生下列意外和并发症:一、术中:1.麻醉意外(包括麻醉时损伤)。2.术中周围组织损伤。3.局麻不耐受改全麻或因患者紧张虚脱停手术。4.术中发现其他病变需改变术式,亦可能无法进行预期手术。5.术中出血、休克、死亡。6.诱发隐匿性疾病发作。7.脂肪栓塞或血管不全栓塞可危及生命或肢体瘫痪、深昏迷。8.心律失常、心衰、休克造成呼吸循环衰竭。9.术中因情况特殊(解剖异常、手术区域离重要组织太近)而行姑息手术。10.术中填塞纱条脱落致气管异物、窒息、死亡。11.目前医学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及路医生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一切术中意外。二、术后:11.术后出血不止、休克,需再次手术止血或清除血块。12.术后感染致伤口裂开、瘘管形成、中毒性休克综合症、败血症。13.鼻中隔血肿、鼻中隔穿孔、外鼻畸形、鼻腔粘连。14.一过性失明、永久性失明、眼肌损伤、眶内出血、眶内感染、眶上裂综合症。15.脑脊液漏、骨髓炎、腮腺损伤、剧烈头痛。16.面部、上唇、齿龈麻木。17.填塞物遗留、脱出,冲洗管移位、脱出,造口闭合,移植组织坏死。18.术后效果不理想、术后复发,需再次手术。19.目前医学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以及路医生不能解释和解决的一切术后意外。三、所有一切其他意外。以上各项已告知患者和家属(或单位)代表。患者和家属单位对以上情况表示理解,愿意承担各项风险,同意手术。并在本记录单签字为证。”
肉球七喜问:“痛不?”
路医生说:“不痛。”肉球七喜的舌头抓起笔,签了字。
后记:寓意
肉球七喜再次醒来,他看到了他的手脚,那么神奇,那么普通,他见了别人的手脚见了五十年,他第一次见自己的手脚。
路医生说:“抱歉啊,手术没有成功,我还是没有赶上我父亲老路。你的手脚能用了,但是还是不能写作和开车。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一切的一切早趁早,尤其是成名趁早。”
肉球七喜说:“我已经很高兴了。能憋住手脚不动,五十年不写,不写也就不写了。”
2008-9-9 02:22 下午
手稿教派

过了三十五岁之后,一两年里会有一两天,再累也睡不着觉,还有好些事儿没做却什么都不想做,胡乱想起星空、道德律、过去的时光和将来的无意义等等不靠谱的事情。这样的一天晚上,我坐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一家酒店的窗台上,五十几层,七、八米宽的玻璃窗户,下面灯红酒绿,比天上亮堂多了,显示我们崛起过程中的繁荣,仿西汉铜镜造型的上海博物馆更象个有提梁的尿壶,射灯打上去,棕黄色的建筑立面恍惚黄铜质地。
心想,没有比人类更变态的物种了。夜晚应该黑暗,眼睛发出绿光仰望天空,人发明了电灯。双腿应该行走,周围有花和树木,人发明了汽车。山应该是最高的,爬上去低下头看到海洋,人发明了高楼。
心想,我被变态的人类生出来,从小周围基本上都是些变态的人类,阴茎细小,阴户常闭,心脏多孔,脑袋大而无当。
粗分两类:和我有关的人与和我没关系的人。和我没关系的,落花尘土,随见随忘,不知道从哪里来到我眼里的,也不知道又消失在哪里了,像是我每天喝下去变成了尿的水。坐在出租车里,有时候也好奇,那个一手公文包一手啃烧饼的胖子,啃完烧饼之后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像是喝着瓶装水望着护城河。
和我有关系的,再分两类,和阴户有关系的,以及和阴户没有关系的。涉及阴户的,情况往往凶险复杂,变态的人类给进出阴户这件事儿赋予了太多心理性的、社会性的、哲学性的内涵,使之彻底脱离了吃饭拉屎等等简单生理活动,比进出天堂或者地狱显得还要诡秘。
不涉及阴户进出的,一拨是亲戚。小时候跟着父母,过节拎着别人送的水果烟酒去拜访,印象最深的是个舅舅。舅舅一辈子所有重大选择都错了,他先上日本人的军校,后来日本投降了,还上过黄埔军校,后来跟了国民党,解放前在青城山投诚当了俘虏,但是起义证书丢了。在文革期间,舅舅被打死好几回,每次都被舅妈用板车驮回来。文革后,每三五天都要梦见找他的起义证书,每次都在找不到的状态下醒来。舅舅书房有个巨大的合影照片,没有八米也有七米宽,刚粉碎“四人帮”那年,还活着的黄埔同学都出席了,没有一万个老头也有一千个老头。我舅舅每次都哆哆嗦嗦给我指,哪个老头是他,每次都能指对了。我还有个大表哥,比我大二十四岁,他婚礼那天,他老婆死拉着我和他俩一床睡,说,这样吉利,这样他们也能生一个像我一样眼神忧郁眼睫毛老长的男孩儿。那天晚上,他俩都喝了好些酒,我出了好些汗,第二天早上醒来,床上还是只有我们三个人,没见到长相和我类似的其它小孩儿。后来,他们生了个女儿,长相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我没有任何相似。
不涉及阴户进出的,另一拨是朋友。我老妈大我三十一岁,我哥大我九岁。我老妈比较能喝酒,我哥比较能打架,他们俩都好人多热闹。我中学下学回家,家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总摆着两桌发面饼之类便宜的吃食和糖醋白菜心之类便宜的下酒菜,酒是拿着玻璃瓶子一块三一斤零打的白酒,桌子一张是方桌,一张是圆桌,围坐十几个人,有的坐凳子,没凳子坐的坐床,陆续有人吃饱了走人,陆续有人推门进来。我眼睛环视一圈,叫一声,哥,姐,算是都打了招呼,然后撑个马扎,就着床头当桌子,一边听这些哥哥姐姐们讲零卖一车庞各庄西瓜能挣多少钱、到哪里去弄十个火车车皮、谁要苏联产的钢材和飞机,一边手算四位数加减乘除,写《我最敬爱的一个人》,看司马迁写的《刺客列传》、《吕不韦列传》。
所以,三十五岁之前,我习惯性认识的朋友基本大我十几岁,我不叫哥哥就叫姐姐,其中也包括这个非官方纯扯淡的《手稿》所涉及的一些人。和这些大我十几岁的人喝酒蛋屄,我常常有错觉,他们的脑袋不是脑袋,而是一个个的水晶球和手电筒,告诉我未来的星空、道德律和时光,指明前面的方向,与此同时,极大地降低了我对未来的期待值和兴奋感。这些哥哥和姐姐们对我的教导,让在我见到女性乳房实体的十一年前,就知道,其实那不是两只和平的白鸽,不会一脱光了上身就展翅飞走,乳头也没有樱桃一样鲜红和酸甜,那些都是哈萨克人的说法。在我每月吃八十块人民币伙食的时候,我就知道,钱和幸福感绝对不是正比关系,一间有窗户的小房子、一张干净而硬的床、一本有脑子的书、一支可以自由表达的笔,永远和我个人的深层幸福相关。
后来,学了八年医,进一步降低了我对未来的期待值和兴奋感。在协和医院那组八十多年历史的建筑里,看见很多小孩子被动地出生,被用来解决他们父母的婚姻问题和人生问题,他们长得一样丑陋,只知道哭,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看见很多癌症病人缓慢地死去,不管他们善恶美丑,不管他们钱财多少和才情丰贫。医院的好几个天台原来都可以自由出入,上接天空,东望国贸,西望紫禁城,但是有太多的绝症病人到了上面不东张西望,不缓步于庭,而是想起星空、道德律、过去的时光和将来的无意义等等不靠谱的事情,一头朝下跳将下去。
再后来,医院的天台就被铁栅栏封上了。
石涛是我最早认识《手稿》的成员,最早认识石涛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手稿》,也不知道《今天》或者《收获》等等非官方和官方文学期刊。
当时我刚从美国念完商学院回到北京,进了一个叫麦肯锡的管理咨询公司。大北窑作为地名已经消失,国贸里面已经开了两家星巴克。上商学院之前,我没听说麦肯锡,没学过任何金融和财务,除了看过一个叫做《血总是热的》类似战争片的工厂管理电影和翻过三分之一《二十四史》,没接触过任何管理。
在商学院期间,1999年暑期实习,周围的人比我平均大二十岁,我每天一个小时就做完了一天要做的活儿,睡多了实在多梦,实在无聊,实在需要忘记一些人和事儿,于是写了六、七万字的半部小说。我想记录1985年到1999年,北京、鸡鸡和心智的生长,就起了个名字叫《万物生长》。2000年,回国后,给在电影学院当老师的发小看了,说,好看,很好看,又说,把我介绍给他的老师张玞和她的男友。我发小叫张玞“先生”,我也跟着叫先生。张玞当时的男友叫石涛,刚做火了一本叫《格调》的书,还做火了杨葵等人人没能做火的上进青年石康,是当时最时尚的出版人,最有潜力的师奶杀手。
第一次和石涛见面是在望京的菜根香,川菜,量足,一般辣。石涛很快看完了那半部《万物生长》,在电话那头,我想象他一挥手,说,写完它。
《万物生长》的下半部在亚特兰大写完,用的是2000年冬天的三周假期。那是一个愉悦的过程,我开不大的暖气,直接喝水龙头里的水,吃米饭和卷心菜。窗户外经常一个人也没有,文字像窗檐上的雨水一样滴答落进电脑,周围花朵怒放,鬼怪缭绕。在十五万字左右的时候,我给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
第一次见到艾丹,是2001年的冬天,是因为石涛。
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常常在人民大会堂请客吃饭,开座谈会,买断大牌作家一生的电子版权。石涛当时是“博库”的内容总监,2001年冬天,为了替“博库”省钱,他领着黄集伟等大小编辑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众作者,有酒有肉,竟然也有我的份儿。
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有男有女,有胖有瘦,都深不可测,都能为世界制造幸福或者灾祸,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
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黑红胖子,一个青白胖子,和一个长得像花生米的黑青瘦子,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穿着白大褂,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他们后来告诉我,他们觉得心酸,原来混迹于医学院之外的社会,是这么艰难。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灌我酒的家伙,一个叫艾丹,一个叫张弛,一个叫狗子,在民间的北京酒鬼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一直谦和有礼,一直在抢酒喝,最后一口真气涣散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一瓶大二锅头,不到半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回想起来,艾丹穿着舒适,和桌子上所有的人攀谈,照顾所有人的酒菜,劝所有人喝酒,鼓动所有人开心。在不经意中,有美女的地方他会多看好几眼,但是手脚并不就势延伸过去。我清楚地记得艾丹看人的样子。基本上是闭着眼睛,但是几乎闭合的眼睛里偶尔放出强烈的光,非常凌厉,时间很短,一瞬间消失,然后是大段大段时间里经久不衰的眼睛闭合着的笑容,普照四方。
第一次见到严勇,是2004年的冬天,是因为艾丹。
艾丹常年盘踞一个代号“食堂”的地方。具体地址是东三环长虹桥往北一百米顺风酒楼北侧一个胡同里,具体菜系时常改变,从川菜到香锅到金华土菜到艾丹自己发明的一些北京菜,具体主人也时常改变,从一个有着外国名字的四川姑娘到一个有着四川名字的四川姑娘到一个不加价两倍从不卖货的古董商人到一个组成复杂的20多人投资群体到一个替这个投资群体装修的精壮靠谱男人。我所在的公司很快显现出它资本主义的罪恶一面,一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很少有时间在北京。我到了北京机场,鼻子闻到尘土的味道,脸贴到干燥的风,就想起喝酒,想起艾丹和我初恋和石涛。当时,我初恋正在闹离婚,促膝谈心或许会谈出不想出的事儿。当时,石涛正在搞创业和闹妇女,见投资者、见妇女、面壁梳理情感问题,似乎比我还忙。于是我总找艾丹。打艾丹的手机,十次有九次他人在“食堂”,十次有九次,酒局还在,“就等你了。”艾丹说。
2004年的冬天,大年初三或者初四的样子,少有的一次,艾丹说,他不在“食堂”,他在一个叫天通苑的小区里一个客家菜馆,“就等你了。”艾丹说。
打车从嘉里中心到天通苑,我才体会到北京有多大。天通苑几乎是个城市,在市中心的所在,找到那个客家餐馆和艾丹。桌子拼桌子,几乎占了半个二层,一半儿以上的人我不认识。我问艾丹,艾丹说,这是谁谁谁,这是谁谁谁。听上去像是听《三国》或者《水浒》,身在其中,鼓瑟吹笙,有笑傲某个地盘的感觉。一个人,瘦,高,微驼,微秃,一直在打手机,才挂断,入席,吃口菜,喝口酒,另一个电话又进来,再离席。我问艾丹,艾丹说,他是严勇。
“他是干什么的啊?”
“他是北大学数学的,和你一样,也做企业,做得很大。和你不同的是,他已经搞垮了好几个企业了,至少有三个,都是xx党的企业,都是xx党的大企业,这就是他一辈子做的事情,我怀疑他是国x党派来的。”
我一个医学院女同学从美国回来看父母,住在北边,打车过来,盛开着粉色的裙子和桔色的大衣,和我喝酒,然后高了,然后和所有人喝酒,然后更高了。我好不容易找了辆黑车把她扔进去,是辆奥拓,女同学身子伸不开,她说,“人生残酷”。我说,“北京真冷”。她开始吐。我兜里正好有一打子十块的票子,准备给各种小朋友当压岁钱的,她吐一口,我就扔两张给黑车司机。
手稿是我见过最古怪的一群人:彼此认识很久,但是互相几乎不了解。多数成员或者有着北大数学系等良好教育或者没有任何高等教育,但是几乎人人都对正经工作有强烈的抵触。有些人一辈子没有任何工作,但是也活着,也有老婆或者女朋友。有些人思考了一辈子人生,写了一本没有一个字的书,妄图在社会主义祖国申请到正式出版书号。手稿起源似乎是一个文学兴趣小组,但是多数人从来不写东西。每个创始人轮流做一次责编,三年才能组齐稿件,出一期刊物,到现在出了三期,但是这项活动竟然持续了十几年,如果照这个速度,所有创始人没有轮到一圈,一定已经有人不在人世。似乎很多人的一个共同愿望是年岁大了之后生活在一起,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公社,由共产党出钱或者自己凑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这个愿望越来越遥远。
我对这一群人,无法窥其全貌。我热爱妇女、文字,练习商业,敬畏古玉。石涛热爱妇女,出版文字。严勇谙熟商业,写过《二月三十日》。艾丹写过《纽约杂记》,热爱妇女,对古玉的天赋远大于文字。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哥哥,我的水晶球。
对于文字,我不认为我应该拍任何水晶球。文字是我的命。这么多年了,一直想摆脱,一直摆脱不了。这么多年了,写一个长篇小说,我的生命之火就死一点。我日老天它妈,为什么是我?一切仿佛我佛,我禅,是我的,别人帮不了。
对于妇女,石涛和艾丹这两个水晶球混沌不清。石涛到底有几次婚姻?现在婚姻是什么状态?女人给他的恐惧大于安慰吗?他在北京的多种死法里,有被前女友们雇凶杀死这一种可能吗?在三里屯南街,我看见石涛抓着酒吧老板娘细嫩的手,问,“我该结婚吗?”老板娘说,“我给你再倒杯黑方吧。”艾丹在传说中那个夜晚,和一个睡名飘香的美女从东单三条一步一步走到东单十三条,在他家院子的门口说,“我忘带钥匙了”。之后的一个说法是,一老一少,看了一晚月亮。关于妇女,我不知道问石涛什么,我不知道问艾丹什么。
2003年后,我也和严勇一样,常住香港和深圳。我在深圳南山脚下有个房子,严勇带过几次酒过去,都是红酒。我们两个心情好的时候,喝两瓶,毫无醉意,眼睛比月亮还亮。我们两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两瓶,严勇就踉跄着下楼,下山,背着月亮,我闻见山林里鸡蛋花的味道,我听见荔枝飞快红熟,我睡到第二天艰难早起,脑子到下午才重新清亮。严勇和石涛对红酒都有研究,谁比谁深,我不知道,但是都比我深多了。严勇只会说好喝或者不好喝,石涛的描述词汇多,胡桃、黄桃、樱桃,仿佛和尚描述素菜大餐,素鸡、素鸭、素鱼。
我问过严勇:“你有过中年危机吗?”严勇说:“当然有,一直有,很早就开始,现在还没好。”后来严勇辞职不工作了,我仿佛看到我不远的将来,我问:“没了收入,如果还想喝红酒怎么办?”严勇说:“喝一百块钱以下的最好的红酒。”我问:“如果一百块钱最好的红酒都没有一千块钱的好喝怎么办?”严勇说:“那就忍住十次,不喝一百块钱的红酒,然后买一瓶一千块钱的红酒好好喝。”
我曾经痴迷历史,觉得时间轴长些,对世事的解读清晰些。我想过一个写当代史的办法,上部叫《垂杨柳》,1949年到2008年,每年引用一段《人民日报》当年的新年贺词,然后让我老妈回忆那年发生的事情。下部叫《食堂》,2009年到2038年,每年还引用一段《人民日报》当年的新年贺词,然后添上每年元旦夜艾丹在“食堂”酒后的发言录音剪辑。艾丹在酒大些、美女多些、倪整姐姐不在的前提下,口头表达水平接近我老妈。
《手稿》第三期很厚,里面有每个人对于一百零一个人生问题的回答和分别在小时候、年轻时候和现在的黑白照片。印出来之后,轮值责编艾丹分外高兴,我管他要了一本,在交给我之前,他执着酒意在扉页写了七个字,“冯唐,怎么办?艾丹”。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