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屋顶 | 己羊的梦
source link: https://www.jiyang00.cn/2019/05/01/roof/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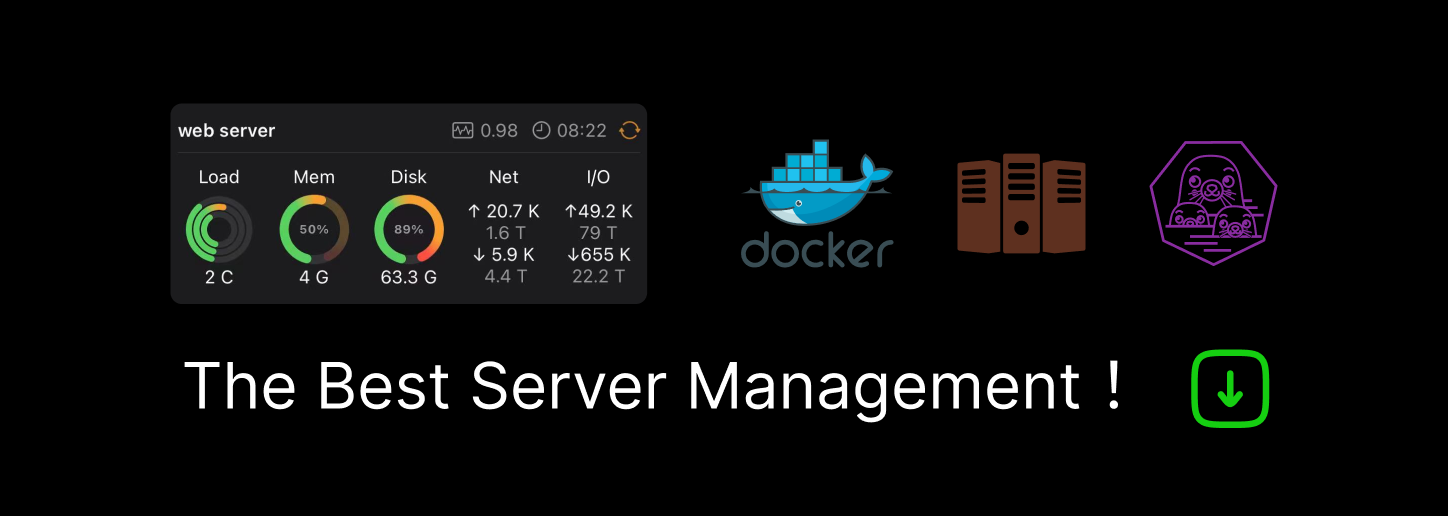

“不孝子送白马一匹、马车一套。车夫一名名顺手,以消除路途劳顿,仆从童男一名名随心,女童一名名如意,供其驱使。另有生活物资数件,金银财宝若干,供其使用。上述物品均属亡人一人所有,他人不得侵夺。敬请冥府对亡人财产予以保护。如有强神、恶鬼、不法者抢夺霸占,请冥府有关部门及时严厉遣责拘押,交酆都城问罪。幽冥有凭,立票为证。”
午后,熹微的阳光穿过屋顶,便被炽烈的灯光驱散,无影无踪。玻璃上残留的余温躲进黑色的缝隙里,灰尘,散漫着,相互碰撞的灰色颗粒,一颗颗蠕动的单细胞生物,变换柔软的身体,依靠,离开。它们霸占着阳光,贪婪,自私,只有一缕残存的光线,透过它们之间的缝隙落下,不明事理的玻璃和自以为是的灯光冲作它们的帮凶,将残存消磨殆尽。
瓷杯中黑色咖啡反射的青色灯光,让人们误以为是阳光还在保留徐徐白烟下的余温。浓烈的甜气充斥大厅,寂静的大厅几乎只听得到门口吧台处一个黑衣白裤把头发梳得油亮的服务生在水池前接咖啡的粘稠的声音,木质地板熠熠生光,不时会听到走路时鞋跟离开地面黏连的声音。
他面前的竖纹木桌上摆了一张英文菜单,上面铺满同一种模样,却标了不同数字(价格)的咖啡图片,和盘子中间只占十分之一的蛋糕,还有蛋糕旁随便涂抹的彩色花纹。端着杯子的服务生瞥向这里,没有过来的意思。所有人都在看他,他知道,即使没有人真的将目光望向他。他们用菜单遮挡着脸,用嘴唇蹭拭杯沿儿,或干脆背过身去。但他捕获到他们的余光,在看错误一样不可思议,诧异的目光,刀子一样的目光,故事里凌迟的传说。他们窃窃私语,他听得到,他的名字。他们以为瞒天过海,天衣无缝。吧台旁的电梯黑色显示屏上红色的数字5,“叮”,所有人扭头望向门口,心虚暴露无遗的展现在他面前。肥胖男子挤了出来,从口袋掏出一部黑色的手机,玩具一样贴在耳朵上。空气中不再是发腻的甜味,沾满毛发的动物,泡在猪油里一天一夜后拾出,暴露在阳光下散发着恶臭。他径直走来,坐在对面,满脸堆笑,从跨在胸前发亮的皮质腰包里,掏出一沓揉得皱皱巴巴的纸摆在他面前。
太阳将余光洒在他灰色布衣上,透过棉絮渗进他的肌肤,他未感到温暖。在没有衣服遮蔽的手臂、脸庞,寒冷似游走的软体动物,钻进骨髓,将身体的余温吞噬殆尽。他立在倾斜的青白玻璃板上,五楼的高度让他被挖去膝盖一般,仅依靠立直的小腿骨和手里杵在地上的拖布支撑身体重量,飘飞的浮尘逃离着这里。他要在离开前清理完这片屋顶,然而即使挪动一步都困难,随时会摔落下去,坠入万劫不复。玻璃下热烈的温度令其蒙上一层白雾,人们在白雾中穿梭,黑色,白色,红色,紫色,色块一样交融,离散。拖布轻轻蹭拭着玻璃表面的灰尘,掠去浓尘后青白色更加浓烈,却依旧看不清薄雾下的场景。胶质鞋底将他固定在原地,却也阻隔了他与身下温度的接触,他感到身下暗暗涌来的温热。跳跃的红色火焰烧透他依靠的火炉,他赤裸身体贴合滚烫的铁片,发出“兹兹”声,红色在眼前跳动,欢腾,飞舞。他感受不到烫,没有烧灼,只有寒冷,从每个毛孔渗进的冰冷的刺痛感,又从每根毛发渗出的寒气。他已融入炉火中,火光将他包裹,青色火焰融化他,他化作火苗,寒冷,依然没有温度。冰的窒息,浸在冰水中,浮冰裹挟着他,坚硬的冰扎进他的身体。烫,滚烫,肌肤燃烧,痛,冰刀扎进骨髓断裂的痛感。不再寒冷,不再炽热。痛,只有痛。灰烬,他化作了灰烬吧。风将他拥入怀中,松散了,没有痛。他拽紧领口,将脖子和下巴缩进衣领,身体倾斜,将身体背向风的方向,抵抗渐渐涌来的风。他看到还未生芽的柳条轻扬起来,迫不及待地离开生养它们的树枝,楼下发动机的轰鸣替无声的风发出它的声音。起风了,他要赶紧干完手上的工作,在风未变大之前,离开这里。黑色布条旋转蹭拭着玻璃,将灰色颗粒席卷到身上,仅旋转了一圈,黑色就染为灰色,灰色布条继续转动,附着的颗粒将灰色挤压至更深处,蹦跳着,逃离着,像是长满腿和翅膀的黑色昆虫,四散而去,躲进玻璃间狭小的缝隙里,被污水黏连,紧贴在玻璃上,不肯离去。
透过雾气,他看到了自己,坐在温热的屋里,对面的胖子擦拭着脸上咸涩的汗珠。肥大的屁股在椅子上留有一半,剩下一半犹如挂在绳上的猪肉耷拉在两边,两条腿像两根催肥的萝卜堆在屁股旁边。外套斜挂在椅背上,被汗水浸透的土褐色衬衫又被肚上折叠的三层脂肪卷进去,衬衫扣子向外挣脱,随时会将衬衫崩解。他一只手攥着几张覆着油的碾碎的纸,另一边则用两根手指缕着他脸上堆积在一起的腮帮上的一根黑须。
“老头儿,我跟你说,——先等等。”他不知道胖子是不是在跟他说话,他的眼神似乎在看自己,又像只是随便望向一个地方便自言自语。他知道他是来找他的,他从电梯里出来,便目标明确,直奔他而来,而且他低俗的称谓在这除了自己也找不到更好的替代者。
他摇晃手里的几张白色旗子招呼服务员,发出哗哗的响声。胳膊上的肉也如同旗子一样摇动着。
“这个,加糖,多加糖!”胖子指着菜单,接到指示的服务生逃离了这里,他是受不了这儿的气味还是觉得与自己接触玷污他尊贵的身份?是后者,是自己,格格不入,异类,像是与这些人不同的物种,身上携带致命的病毒,仅眼神的相触也会让他们万劫不复。
“老头儿,我跟你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胖子的语气愈发不客气,脸上笑意却越来越明显。他又开始捋那个黑须,鬃毛一样的黑色长须,一根坚硬的毒刺,他随时会拔下来扎向自己。他咧开嘴露出黄色牙齿,散发腥气,他闻不到了。胖子不见了,他走了吗,没有得到回应气愤离开?对面男子宽阔的肩膀背对自己,深蓝色呢绒西服没有一丝褶皱,垫高的肩膀显示雄壮的身躯。他的眼神也在躲避着自己,为什么他要坐这儿呢,猪鬃的气味还没有散开。为了看我的笑话吗,他为什么不转过来当面看着自己。
他接过胖子递来的空白合同,白纸边缘发黄的几个手印,纸上的字犹如蝌蚪一般在白色湖泊中穿梭,密密麻麻的小字间留有几个空隙。“老头儿,在空里填上你名字。”
他看到他儿子转过身来,“儿子。”他喊着,人们不再讥笑,他们露出自惭形秽的表情,被观摩的猴子跳出笼子站在人们头顶,露出紫色的牙龈。猪鬃气味淡了,甜腻的味道又重新浮现出来。他把菜单递给他的孩子,他知道他一定都能看得懂。
胖子的脸开始扭曲,他毫不掩饰的表达自己的兴奋,身上的汗迹覆盖的面积更大了,顺着胸前流淌下来的汗被卷进肚子。他在笑什么?他在那几张白纸上写着什么?肆意的野猪,贪婪懦弱的野猪,只敢把身躯欺压在比他弱小的动物上,遇到真正的草原之王便四散而逃。
风变成刀子,钻过衣服剌在手臂上,冰冷将还未流出的血冻住,封住伤口,再将凝固的血块撕开,冲击皮肤,搅动他的血肉,将他的骨头震裂。太阳这时躲了起来,躲避风和寒冷的肆虐,所谓阳光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拖布沾满灰尘,不再有颗粒附着在上面。他提着拖把回到屋里,打算躲过风后再回到屋顶。木门上的铁门栓叮叮当当,他手机也叮叮当当。“别偷懒,赶紧干活!”臃肿的声音传来,黑色的油迸发出来。他拖着拖布回到屋顶。路旁的树抵抗风的摧残却无奈弯下了腰。风声从无声变为清晰可闻的呼声,挂在脸上,不再像刀子一样划过皮肤,而是重拳一样一拳一拳锤击着脸上的骨头。他背过身,面向楼底,用背抵抗着风。他将拖布放在胸前,脆弱的拖布腐蚀不堪的身体还要支持这个人的重量。楼下的人浮絮一般顺着风的方向奔走,躲避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玻璃下的人们却悠闲地喝着咖啡,完全没注意到即将来临的是什么。他们抬头看着他,脸上露出讥笑的表情。他看不到他们,玻璃将他们身影完全模糊,他知道他们在笑。他不由自主地向楼下迈了一步,胶质鞋底不再加大他与玻璃之间的摩擦,玻璃像液体一般流动着,他的身体陷入其中,波浪锤击他的小腿,让他不禁前拥而去。他有些后悔从门后走出来,他想把身子转回去,风拒绝了他的请求,加大力度将他身体向前抛去。
笑吗,他们还在笑着,笑他的软弱,笑他自不量力,笑他蚍蜉撼树。他的儿子没有笑,甚至没有看他。他手里的白色瓷杯透出更白的光亮,光本来的颜色,刺眼,无尽的白之下是什么颜色。
他为何不看自己,只是低头在看手机。老家院子前那颗桃树上,蜜蜂开始采蜜,桃花散发花香,翅膀振动的嗡嗡声。又开始议论了,肆无忌惮,变本加厉。他们像抓住了把柄,不再惧怕和他眼神的相触。一个个挖心的钩子,刽子手上挑得眼睛盯着他,狼看着自己即将到手的肉,钩子在磨石上变得锋利无比,冷岑岑的青色光芒,一声声金属与石料摩擦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人们脸上的讥笑,不再掩饰的声音,他低下头,不敢再看,他浑身颤抖,即将被绞刑的犯人,看热闹的人群。他的儿子依旧没有抬头。你也怕了吗,你也感受到一双双恶狠的眼神了吗。不,你不会怕的,你身份高贵,比他们有过之无不及,又怎会害怕他们,你只需看他们一眼,他们就会溜走。
人们的声音穿过他的耳朵,扭动的空间让他窒息。
“你快走吧!”女人尖锐的声音刺破幻想,昏暗的小屋摇摇欲坠,低斜的阳光无法将这间屋子照耀得透亮。女人的声音屋子里回荡着,像清晨绵长的钟声一样令人昏昏欲睡。余音消散,消散到空气中每一粒分子中去,化为压抑的空气中的一部分。儿子将他的目光藏在那缕低斜的阳光里。女人的声音回荡在他耳边嗡嗡作响,她在说什么?他在看那缕阳光,他想从阳光中找寻他儿子的踪迹,看清他目光尽头是什么。小孩儿的啼哭像一把利剑划破凝固的时间。他的儿子站起来,不再将目光隐藏起来,低头俯视,眼神中的色彩留在昏暗不明的阳光里,空洞的眼神包裹着他。“你走吧。”儿子的声音宣判他的死刑,他在这里不再拥有一席之地,没有任何过错。女人的声音还在远处震荡不停,似乎喋喋不休就能将她变得理直气壮,孩子的啼哭音也像一曲索命的歌曲,伴随女人的咒语。“走啊!”儿子的声音不再理性,情绪开始不受控制,眼神不再空洞了,愤怒,仇恨,一些东西开始流淌。他的脚上没有力气,这间屋子像一个巨大的胃,柔软,阴沉,酸臭,他踩在地上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他挪动着步子向外走,踩着棉花般的虚弱感让他感到自己每一步都可能跌倒,女人的声音停止了,余音还在飘荡,她的脸上露出笑容?孩子般的笑容?天真的笑容?孩子哭声也停止了,用沉默庆祝胜利。空洞回到了儿子眼中,他将一切情绪还回给阳光。冰冷的金属扶手给了他这间屋子中唯一真实的感觉,在冗长而纷杂的气氛中,屋里与屋外的空气接触了,屋内的空气开始不再浑浊。屋外更加昏暗,冰冷瞬间刺破肌肤。他听到窗外的风敲打着玻璃想冲进来躲避寒冷,可连他都要离开这里,他们来了又何处藏身呢。门关了,寂静,没有女人的声音,棉絮一般充斥着空间撕扯不开的声音,没有孩子的啼哭,也没有了儿子的眼神,只剩下寒冷,饥饿,还有无尽的属于他或不属于他的时间和空间。
现在儿子坐在对面,眼神依旧空洞,从那天开始他眼中便没了色彩,留在那片阳光中,被带去不知什么地方。他抛弃他,将他赶出去,让他衰老的身体暴露在凛冽的风和瓢泼的雨中。现在他看着父亲像猴子一样展览,他眼中依然激不起一点的波浪。相比他身后充满恶意的眼神,这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神更加恐怖。空气中苦香味更加浓郁,他站起身来,抽掉椅子,空洞的眼神接纳所有人目光。他走了,来时不知所为,去时也不知所以。
胖子粘稠的声音又响起来,听不清。老人感觉自己陷入一片沼泽,身上粘连腥臭的泥浆,身体下陷,柔软的泥浆深不探底。泥浆将他的膝盖没过,将胸膛包裹,将脖子锁紧。不能呼吸,他感受不到空气继续提供的养分,他只得大口喘着粗气,将身体中仅存的一点气体呼出。人们不再注意他,将死之人能吸引别人多大的注意呢,对面的那个胖子还在喋喋不休,似乎他并非在对老人说话,而是通过说话他才确认自己存活于这片时间中。“老头儿,我跟你说,这合同签好了。”胖子喝了口咖啡“你要是违约,得赔钱。”他只听到这句话,他为什么会违约,如果不接受这份工作,难道要露宿街头,沿街行讨吗。胖子又嘟哝着什么,似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他说的。他没有在听,他在用尽力气挣脱着,酸臭的气味钻进大脑,肺部被挤压得容不下吸取一丁点氧气,他窒息了。
他羸弱的背部承受不住变得更猛烈的风,他的骨头违背身体的旨意,土崩瓦解,散开的骨架纷纷要从包裹着的皮肉里逃脱出来。他摔倒了,重重地摔在玻璃上,一瞬间惊吓到正在看戏的人群。拖布挣脱开钳制它的手掌,向前滚去,缠在一根从屋檐下延伸而出的细铁杆上,飞起,落下,敲打玻璃发出清脆的声音,接着消散在风中。他俯爬在玻璃上,用身体所有重量,手掌的黏性和鞋底的摩擦力,抵抗着风。屋里的人们纷纷抬起了头,他们不会错过这出好戏,这比他们装模作样坐在那儿将自己扮演成一个社会里不可或缺的人可有意思的多,甚至有人起立向他鼓掌,叫好。好戏上演到一半,人们的热情变得空前高涨,所有人都在为他加油,或者说为风加油,他们都想看到那一幕。老人听不到这些,他只听到呼啸的风从他身边飞驰而过,在他身边喊着,“放弃吧,老头儿!跟我去吧,没什么值得你留念了。”老人咬紧牙,不让这声音钻进他心里,他扒着玻璃间的缝隙,指甲插进缝隙中,手背青筋暴起。风中卷积着黄沙将他脸上的皮肤划开一道道的口子,进入他的血液中。缠在铁杆上的拖布撕扯着,可以听到布条断裂的声音,铁杆坚持不住风的力量,挣脱了,滑落了,拖布沿着倾斜的屋顶滚落下去,不见踪影。老人也到达了极限,风将他的手指一根根撅起,颤抖的手指再不能发挥力量,他只能用鞋底继续支撑身体。风被他这近乎嘲讽的举动激怒了,更加狂暴的狂风席卷而来。他听到路边还未成熟的树被拦腰折断,轰然坍塌。他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开始倾斜,向下划去,他甚至感觉要飞起来一般,胸腔贴不到地面。抓住了,他握住了细铁杆,铁杆被他拽得弯曲倾斜,可也足以固定他的身体,直到风败下阵来。
安心了一些的老人,透过玻璃,看到胖子摇晃着他两颗肥硕的屁股离开了。
人们不再看他,他们站起身子,抬头盯着屋顶那个握着铁杆的老人,脸上露出惊恐,疑惑,担心的表情,他盯着胖子留下的黑色咖啡的一圈圈波纹里倒映的人群,他只看到欢喜,期待,迫不及待。虚伪的人们带着面具存活在这世上,否则将寸步难行。他在倒映的咖啡杯中看到一个姑娘微笑着从门口向他奔来,她没注意到人群,没注意到屋顶的演出,她瞳孔所容纳的,都只有他的影子,她脸上的表情最后都汇集到嘴角边两颗深深的酒窝里,老人看到了那个微笑,不同于其他人的笑。女孩坐在胖子坐过的地方,柔弱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她随意摆弄着菜单,眼神却不在菜单上。她什么也不说,就只冲他笑。眼眸像春风吹皱的湖水,清澈透亮,明眸涌流。他在她眼里只看到自己,他也暂时忘记周围正在看戏的人群,许久未见,一颦一笑,两颗酒窝,熟悉而安心。女孩捧着菜单离开座位,轻盈的身体显得她格外羸弱。回来后的女孩双臂相叠撑在桌前,微笑地望着他。服务员拖着黄色的底盘走来,眼睛向上瞄着。咖啡自然的被放在女孩的身前,浓郁的黑色中白色雾气升起,她将咖啡杯推到他面前,白亮的陶瓷釉色照映女孩纤细的手指。苦涩的气味带入他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闻咖啡,他不明白为何人们爱喝这苦涩的东西。女孩依旧没有说话,一双眼睛期待得望着他,两个酒窝深深扎在嘴角两侧。他小心得捏着透亮的圆把,举起杯子,用嘴唇前端一点可以感受到味觉的部位,触碰这杯黑褐色的物质,女孩笑得更开心了,她的眼睛弯成月牙的形状,两排牙齿像他手中瓷杯一般透亮。苦涩味儿中夹杂一丝香甜。
“不孝子送白马一匹、马车一套。车夫一名名顺手,以消除路途劳顿,仆从童男一名名随心,女童一名名如意,供其驱使。另有生活物资数件,金银财宝若干,供其使用。上述物品均属亡人一人所有,他人不得侵夺。敬请冥府对亡人财产予以保护。如有强神、恶鬼、不法者抢夺霸占,请冥府有关部门及时严厉遣责拘押,交酆都城问罪。幽冥有凭,立票为证。”
火光前,一匹青白纸马,纸碎被风吹得铃铃响,火光从脚燃着,蔓延全身。黑色的雨,助燃青色的火。他独自一人跪在墓前,低矮的松树沾染尘土的灰暗。身前一排青白色墓碑,离他最近的,他妻子的名字。黄土掩埋他的膝盖,他坐在脚跟上,不远处那匹高头大马焚烧殆尽,纸马旁两排人跪在墓前,那边传来女人的哭声。他没听到,眼神呆滞得盯着墓碑上的字,他看了一辈子的两个字,现在已经从他的记忆里抹去了,那两个刻在墓碑上的图画,让他联想不起任何和他记忆有关的事。松树扎在碑前,一边被烧成黑色,它的生命也即将结束。他的膝盖陷落在湿润的泥土之中,他的灵魂被这片土地抽离,养育了所有人的泥土,最终他们还会将自己归还于你。火光消失了,哭声消失了,焚烧过后的黑色纸屑消失了,阴沉的天空笼罩了刻在石碑上的两个字,淅淅沥沥的雨打在石碑上。他的膝盖开始生根,他化为墓地之中一棵松树,代替着那棵完成使命的松树陪伴这块孤独的墓碑。
风耗尽力气,他躲过了它最猛的势头,铁杆被他攥的折弯了腰。仰头看戏的人们,眼神中充满失落,鼓掌的人也早把手臂垂下。他手心蓄满了汗,手指也被划破,他笑了,想象着脸颊上的两颗酒窝,他松开手,风已不足以将他吹动,而他却向下滑去。第一个人开始尖叫,他们大声庆祝,风的胜利就是他们来之不易的胜利。他看到楼顶边缘,那并不是垂直的墙壁,楼下奔跑的人们,他们看不到头顶一个生命在与他们一起抵抗风的肆虐,不,他不再抵抗,那双纤细的手轻推着他向前行去。黑色的血,在黑色的雨水中流淌,人们肆意践踏脚下分不清是雨还是血的浆液,溅起来的水花浇筑他们的身体,四分五裂身体,被虎视眈眈的围着,草原上的狮子,唾手可得的肉,腥臭味儿在空气中发酵,令人沉醉,那比咖啡更诱人的血腥味勾引着人们的魂魄。警察驱散围观的人群,人们恋恋不舍地回身望着即将到嘴的肉,他们在远处觊觎着这里。玻璃下的人们露出更惊喜的笑容,白瓷杯里的咖啡荡漾着,破碎他的脸,他的脸在杯子里被搅得破烂不堪。风肆意的狂笑,萧萧风声席卷着它所接触到的一切,树叶奏出一曲悲鸣的丧歌。散了,滑落。那副笑容,那对酒窝,那双纤细的手臂,欢迎他的到来。张开双臂,羽毛翻起,露出红色皮肤,顶风前飞,顺着风的纹路滑翔而上,席卷而回。他离开屋顶,化作羽翼未丰,对抗风的鸟。他看不到陆地了,眼前只有黑色,无尽的黑色。黑色包裹着他,保护着他。安详,他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原始的黑色像母亲的怀抱,将他揽入怀中,用温暖宽阔的胸脯包裹着他,一阵阵风吹动着他,抚慰他的身体,他的心神安宁,像刚睡醒的婴儿,未睁开眼,仅凭感官感触初识的世界。耳边“嗡嗡”的电钻的声音,黑黢黢的空洞,白色的大褂,口罩遮挡下的笑容,他在笑吗,笑自己哭得像个婴儿,消毒水刺鼻的味道令他沉醉。前面是什么?黑色,黑色包裹着他,将他揽入怀中,摇晃着他,是什么。爱吗,是无尽的原始色给世间万物无差别的爱吗。
人们围上来,低沉冗杂的声音为他演奏安魂曲,警笛也加入伴奏。人们四散而开,雨冲刷了血迹。
我扣上书,离开座位,屋顶的人已经离开,没有了翩翩起舞的身影。阳光刺入我的眼睛。阳光,自诩光明的使者,天神的儿子,将温暖洒向人间,驱赶着世间的丑恶,殊不知,那无穷的黑色才是世间本来的颜色,他孕育出世间一切,一切美好,丑陋皆出于此。他们像母亲一样包容一切,无论是谁。而这光明,只接纳它所容许的,所谓驱散邪恶、阴暗,无非是将它不能容忍的驱赶出他的身体。
斑驳的血迹前,鸟一样的身躯。风给他无尽痛苦,又给他无尽快乐。玻璃下的人们还在摇晃手中的咖啡杯,无所顾忌地披露着虚伪奸诈,阳光一样笑着温暖着周围的人。风雨飘摇下阴暗的人们才是真实的,他们展现最真实的快乐,痛苦,阴暗,和光明。在他们身上,才有着希望,生命中最本真的希望。
他化作穷奇,传说中的异兽,外形似虎,生有一双翅膀,能听人语,闻人斗则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生于天地之间,风便不能成为让他丧命的缘由,阴暗混沌中生长。生于光明下的人们,遇见他便暴露自己的本质。仁义道德,善良正直,都不及能在死亡前,昂胸抬头,直面死亡。人之将死一刻,谁又能恪守准则。他在阴暗处抖动身子,毛发沾满露珠,钢针一样根根竖起,未生羽毛的两扇虎翼刻出骨骼的痕迹,顺着脊背伸至翅膀末端,两排尖牙上面生满黑色的斑迹,那是善人的血干固在了上面。狂笑,虎吟震天,在山林最阴暗的角落栖息,食天下至善之人,扬天下至恶之人。
他走过来,握着拖把,露出微笑,衣服一丝不苟,翩翩起舞。
风停了,他随风飞去别处,太阳出来,驱散阴翳。
二零一九年五月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