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和国家,历史学家徐国琦看到的中国人和美国人 | 访谈录
source link: https://www.douban.com/note/712149704/?_i=5456826TSL5Ir_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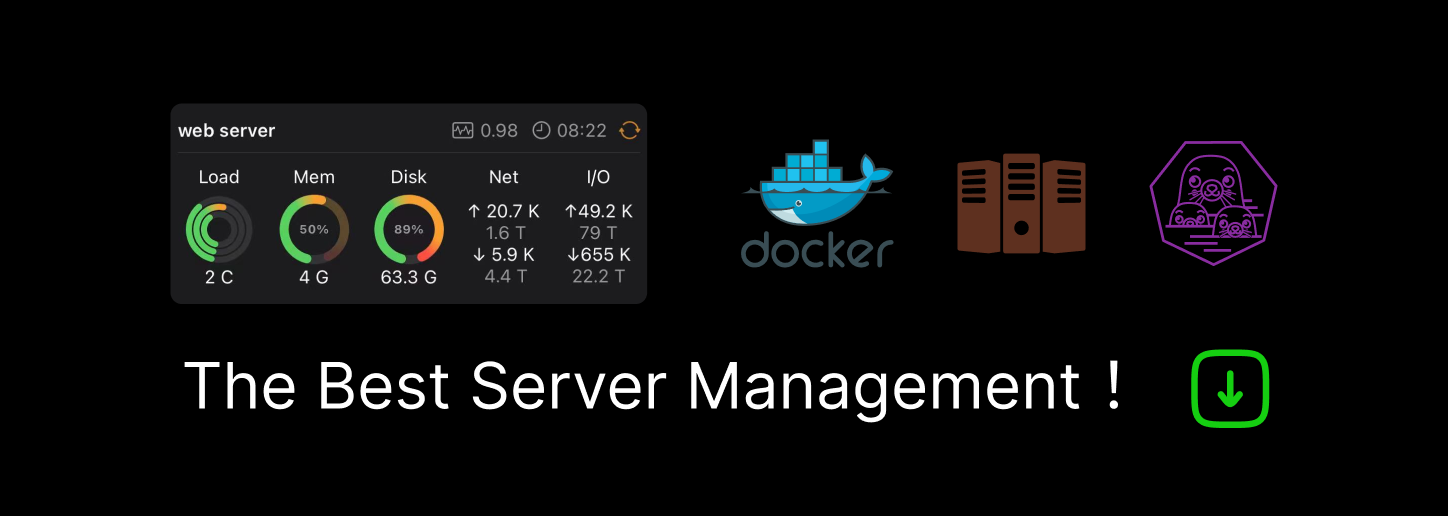
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和国家,历史学家徐国琦看到的中国人和美国人 | 访谈录

本文作者: 曾梦龙
对徐国琦来说, 2019 年是个特别的年份。
一方面,从个人角度,这一年是他离开中国大陆的第 29 年,意味着已经超过了他在大陆生活的时间,更彰显了他自认为世界公民和边缘人的追求;另一方面,从专业角度,这一年也是众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年份,包括五四运动和巴黎和会 100 周年、中美建交 40 周年、冷战结束 30 周年等,身为历史学家,他有许多感受与反思。
徐国琦是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著有多部中英文专著,包括《中国与大战》(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一战中的华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中国人与美国人》 (Chinese and Americans)、《奥林匹克之梦》(Olympic Dreams)、《亚洲与大战》(Asia and the Great War)等。
徐国琦的人生带有些许传奇和励志色彩,他曾在中文学术自传《边缘人偶记》中详细回忆了自己的经历。
他 1962 年出生于贫穷落后的安徽省枞阳县下桥村。“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此前基本不读书的他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出农村与贫困,于是开始玩命读书,成为了 1980 年枞阳县的高考文科状元。但是,由于高考英语成绩几乎为零分和缺乏填报大学志愿的技巧,最后他阴差阳错地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1984 年,他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攻读美国外交史硕士学位,师从杨生茂先生,认为是其“真正读书的开始”。硕士毕业后,徐国琦留校任教。到了 1990 年,他离开南开,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导师是国际史大家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 1999 年博士毕业后,他前往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学院(Kalamazoo College)任教 10 年后,于 2009 年去了香港大学任教至今。
因为做的是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徐国琦称自己的学问“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国际史和共有历史都是新的史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国际史的追求及旨趣是要“跨学科、踏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希望彻底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约束,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之作用与影响,强调多国档案研究和“自下而上”的方法。共有历史则是国际史方法的进一步提升,着眼于共同的历程及追求,侧重文化范畴,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也是徐国琦的发明。
“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人,我们必须要挣扎出自身或外加的各种束缚,如出身、宗教、语言等。……对于我这种做跨国史和共有历史的学者来说,世界公民的特质尤其重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的职业和研究方向决定了我是一个世界公民。”他在《边缘人偶记》中写道。

除了世界公民,他也觉得自己是个永远的边缘人,比如生在贫穷的农村是边缘;在美国念书、教书和写书的中国学者也是边缘;在香港这样不中不西的地方任教,不会广东话的他同样是边缘;甚至知识分子就应该主动处于边缘,才能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当然,所谓边缘,永远都是相对的,比如徐国琦的学术成果绝对不是边缘。他曾获日本协会(波士顿)所颁发的重光葵奖,肯定其在当代亚洲国际关系研究和著作方面的突出贡献;他目前所出的 5 本英文专著都是由西方顶级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认为自己的一些研究成为了标杆,其他学者要进入这个领域,很难绕过去。
他称,自己一直在追求林语堂当年“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之境界,希望找到东西文化之间的立足点,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
2019 年 1 月,徐国琦的英文专著《中国人与美国人》(Chinese and Americans)被翻译成简体中文出版。这是他“共有的历史三部曲”第一本。这本书从“共有的历史”视野出发,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六个个案,“揭示中国人和美国人共有的历史过去如何为民族的发展追求带来影响,指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同经验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
他认同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的看法:中国和美国互相需要,因为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都无法承担与对方分道扬镳的损失。
“历史,即便是共有的历史,也不会如老旧的教科书为人们提供‘教训’。但是它的确提供了种种实例让我们借鉴,让我们从中得到鼓舞或记取遗憾。当中国人和美国人踏上前方充满危险的旅程时,这样的历史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指南。”他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中写道。
2019 年 3 月,我们和远在香港的徐国琦做了一次电话访谈。访谈中,他的普通话带有安徽口音,还和我们开玩笑说“胡适是安徽人,你要听胡适的中文,比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乡音难改”。
在他看来,《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理想是接续第一本研究中美关系的书——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 1948 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希望从国际文化主义角度全面梳理中美关系史。
因为局势变化,这本 2014 年的书在今天被翻译成简体中文出版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我对中美关系抱有乐观,但是不乐观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在中美关系这个转折关头,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今年 57 岁的徐国琦对《好奇心日报》说。

Q=Qdaily
徐=徐国琦
民国宪法顾问古德诺在 100 多年前有什么洞见?
Q:你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中讨论了六个个案,我读完后,对古德诺和杜威两个个案比较感兴趣。先说古德诺,你梳理了许多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但历史学研究重在揭示真相,所以你也没有表达对他看法的思考。你愿意分享一些对古德诺看法的思考吗?
徐:我所有的书实际上都有一个特点,用故事说话。尽管我有比较大的学术视野或关怀,但是我一般来说是跟你说个故事,所以这本书我讲了六个故事。从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到古德诺、杜威,然后还有一个整体的体育,即体育作为国际文化如何造就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共同历史。这六个题目环环相扣。例如没有蒲安臣,就没有后面的留美幼童故事,也可能就没有古德诺来华。
古德诺来华跟哈佛前校长访华有关。1912 年,哈佛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代表卡内基基金会访问中国、日本。他告诉中国政府说,基金会愿意为中国寻找最优秀的宪法顾问,帮中国建设新国家和制定宪法。在中国期间,艾略特正好见了两个人,一个是唐绍仪,当时的民国总理;另一个是袁世凯的心腹,叫蔡廷干。这两人都是留美幼童出身,英文非常好,大权在握。这两个人在相当大程度上促成了古德诺最终成为中国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来中国,任务是帮中国制造宪法。而且非常有意思,当时中国激进派控制国会,想仿效的宪法模本不是美国宪法,而是法国宪法,所以要找法国宪法专家。古德诺对中国一窍不通,也不是法国宪法专家。他 1882 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专长是比较,是行政法。但因为种种因缘聚会,他被选上了。
古德诺本来在中国的任期是从 1913 年到 1916 年,但实际上在中国待了一年就走了,借口是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但他名义上一直做中国顾问到 1917 年。他的确提供了宪法草案,见到袁世凯,跟好多中国上层人士交流,尤其跟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经常交谈。所以,他当时近距离接触中国最上层,给美国国内写的报告或信件是研究当时中国政治外交非常好的素材。但是,据我所知,国内学者很少人利用这批档案。同时,美国政要问古德诺的问题和信件也反映了美国人对华的思考。
尽管古德诺来中国之前,从没关注中国,一无所知,但一无所知有个好处,他没有先入之见,有求知欲,会观察。所以他来了之后,看了,最后得出很多有趣结论,也有很多疑问。他的结论说,当时中国可能完全变成民主国家不见得成熟,但中国不管什么政体,关键是法治,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去做。他说,你称帝也好,共和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不管什么社会、背景、体制,你都要在法律框架下去运作。没有法律框架,最后就是一盘散沙。而这一点过去大家隐隐约约提到,但是很少有人通过他个人观察、报告去梳理、去看。我在这一章引述原始文件比较多,通过他自己的长篇通信、报告、观感去说话,想让他自己说话。
我之所以说故事,不讲个人看法,因为历史学家最怕有先入之见,我的特点是让大家读完故事,然后自己解读我想说明什么。你读之后,想一想,就像橄榄果,有很多回味。我不像一般的历史学者好为人师,告诉完这是怎么回事,什么结论。我一般点到为止,但是故事本身内容很清楚。
所以,你真要让我去解读他的洞见,我会告诉你,他有好多洞见。直到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反思 100 多年以前这位美国人的所见所感。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好多问题可以浮现在脑海里面。我想,既然你提到这个问题,你的脑海里面应该也有好多问题。况且大家知道这几年好像袁世凯变成敏感词了。我没仔细读中文版,不知道它有多少删节。如果要是完整保留下来,大家读完了,尤其借古德诺之言,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让中国人思念德、赛两位先生应该是杜威的最大贡献
Q:再说杜威,你说:“或许最大的讽刺在于,杜威竭力想要改变中国,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最终改变最大的却是他自己。”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讽刺?
徐:杜威到中国来也是阴错阳差。 1919 年,杜威 60 岁。他的学问、人生到了转折点。他 1918 年学术休假,到日本演讲了几周。他的中国学生,像胡适一大批当时在中国呼风唤雨的前哥伦比亚学生听到这个事之后,邀请杜威到中国演讲。杜威刚开始到中国,就像他的哥伦比亚同事古德诺一样,对中国一无所知,过去没来过,中国也不是他的研究领域。但他来了,而且他到中国的时间非常有趣。他 1919 年 4 月 30 号到了上海,那天列强把山东给了日本。 4 天之后,五四运动发生了。杜威本来在中国只想逗留几个星期而已,最后一待两年多。他一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的 1921 年 7 月底才回国。
所以,中国之行改变了杜威,这么说一点不夸张。第一,除美国之外,杜威生活最长的国家就是中国。第二,杜威根本不是个好的演说家。当年美国联邦调查局跟踪他,说杜威演讲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但他在中国的演讲风靡全中国。为什么?他的演讲绝大部分通过他中国的天才学生胡适等人翻译,而这些中国学生借杜威之口贩卖私货。杜威离开中国之后,他俨然以中国代言人自居,回去经常给美国写关于中国的看法。他摇身一变,变成中国的专家、中国的朋友。二战期间,他垂垂老矣,还想访华,为中国的抗战作出贡献,但因为健康原因,不来了。
最大的讽刺是 1949 年之后,杜威这个名字变成敌对的(名字)。所以,他一心想改变中国,看看现实,最起码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改变。因为杜威在中国,不仅是胡适的老师,还作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化身,所以都是讽刺。到今天,我们还在寻找德先生和赛先生。杜威 1952 年去世。他去世的时候,中美在打仗。另外,我在书里面也提到这样一个悲剧。胡适为了表示对杜威的热爱,把他的小儿子取名胡思杜,即思念杜威。但是,这位思想比较激进的儿子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结果因政治迫害于 1957 年就自杀了。
这个东西没法展开,但这里面的故事就跟古德诺一样。尤其像你说的,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杜威在他的演讲里面,实际上非常反对社会主义。后来我找到他当年受美国政府委托写的中国国情报告,他觉得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功,也反对。但是,历史最后是另外一个样。他一心所说的教育救国、德先生、赛先生,在目前,还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Q:你说:“或许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现在到了重新思考杜威作为中国人和美国人两方面的代言人所起的作用,以及从他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时候了。”今年恰好是杜威访华 100 周年,你觉得我们能从他的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
徐:我觉得德先生、赛先生还是需要的。因为 100 年过去了,这两位先生在中国好像从来没有正式现身。让中国人思念两位先生应该是杜威的最大贡献。另外一个,别忘了,杜威在中国是 60 多岁,跑遍了中国 18 个省,做了将近 500 场大小报告。你说他是影响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影响他,还是互相的?而这一点,我们今天,尤其蒲安臣、古德诺、杜威这三个美国人,平心静气地说,他们是想帮中国做些事。后面两位都是学者,有批判性,但也想帮中国做些事。
所以,杜威到中国来,扮演了三个角色——使者、学习者、教育者。不管是中国人或者外国人,这三点实际上很重要。他等于是虚心学习、观察、求教,然后真心分享,并不强迫你说他就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学者在这一点上很欠缺。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一个真正的智库?我们有跟美国学者一样那种智库型的人吗?当然,你可以说有意识形态、政体之分,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美国研究学者自己愿不愿意扮演刚才我说的三个角色?

现在,民族主义反倒变成今天五四所谓的重要遗产
Q:刚一直提到五四,你之前有过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没有一战,何来五四?”,认为五四在中国一直被政治化,所以需要历史学的探索。但是,《西湖》杂志那篇访谈是 2009 年,也就是五四 90 周年的时候做的。现在 10 年过去了,对于五四运动,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徐:那时我觉得,研究五四的时候,很少人把一战放进来,更不会把一战华工放进来。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它是客观存在。没有一战,怎么能有五四?五四爆发直接跟一战有关系。因为中国在一战战后和平会议上所谓的失败,梁启超先生把这个结果发了一个著名的电报回国,才有五四。五四跟中国的一战诉求是一脉相承。
讲五四必须要讲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之后,保守也好,激进也好,大家都认为大清王朝不可救药,中国必须改。中国在 1912 年成为所谓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供奉的两个榜样就是美国和法国。从甲午开始,朝野为之一变。也因为甲午,在中国才有你们所谓真正的媒体。
所以,从甲午到五四是一脉相承的。一战爆发之后,中国人认为机会终于来了,套在中国人身上的帝国主义绳索有可能被取掉。因为帝国主义阵营本身在打仗,一战理论上是西方文明内战,西方国家打西方国家,然后再变成世界性(战争)。所以中国认为旧的国际秩序在崩溃,新的秩序还没有形成,那么中国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不仅可以民族振兴,还可以成为平等国家,然后派了 14 万华工去了,派了最优秀的人到巴黎和会去了,最后中国人认为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失败了,于是才有五四。
所以,不从一战,不从国际环境,不从共有历史或者国际史这个角度,你讲不清五四。我们过去(因为)意识形态,不讲一战。因为一战在中国,过去认为是坏战争,是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北洋政府是坏政府,是卖国政府,没法心平气和讨论五四。现在因为不能讨论德、赛两个先生,那更没法讨论。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可惜我们也没法好好反思。这里面有太多东西需要检讨、思考,要让我们去改变某些东西。
Q:那你能展开讲讲具体哪些东西是需要检讨和思考的吗?比如我看你之前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激进政治的开端。五四之后,中国的政治集中化,意识形态集中化,学术思想集中化,政治行为暴力化。
徐:五四后来在中国变成激进的代名词,而激进对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是好事。因为你不成熟。就像刚才说的古德诺,古德诺也认为当时中国教育不发达,中国社会缺乏民主积淀,不可能一下成为真正的共和制民主。你一激进,实际上这个药是不对症的。最后因为激进,一战之后,越南、中国、俄罗斯、北朝鲜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有些国家,像日本一战之后成为所谓五强,然后二战被打得一败涂地,然后又变。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一样。一旦冒进、激进,都有问题。我觉得激进如果作为五四所谓的遗产,应该反思。后来我们付出很多代价,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是激进的结果。
五四实际上还有个大的遗产是什么?平民教育。而我们今天变成扫贫,政府要消灭贫困。实际上,那时他们也要消灭贫困,但是像晏阳初他们怎么做?他搞平民教育。教育不仅是教你识字,还教你怎么成为公民。我们今天有这方面做法吗?那还是 100 年以前。这也是杜威的实验论、新教育法。
我们现在有几个人意识到晏阳初的伟大?晏阳初当年帮助一战华工,觉得中国人缺的是教育,于是他在回国之后,一辈子献身平民教育、乡村运动,梁漱溟、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运动,同晏阳初一脉相承。平民教育才是五四的优秀遗产。我们今天绝对可以借鉴。我来自乡下,但越来越发现现在的乡村不是美丽乡村,而是空壳化,都是留守老人、小孩、妇女。另外,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过去的一些美德都没有了。我们该不该回到五四平民教育、乡村运动?怎么治理?
所以,这里面说起来太多。我个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往下深谈,有好多可以检讨的地方。我做的历史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不太喜欢谈那种所谓大的政治。民族主义变成今天五四所谓的重要遗产,但民族主义实际上弄不好就是个坏东西。

分歧冲突只是一方面,对于“共有的历史”应该有更多关注
Q:你写作《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现实关怀是希望能为中美开启更好的共有未来提供一把钥匙。但正如你的导师入江昭教授在序言中提到的,国际关系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存在分歧和潜在冲突,另一个是无限的跨越全球的交往。所以我看有人会质疑,觉得你把中美关系的未来寄托在文化上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
徐:不算太理想主义吧?我提出“共有的历史”,并不表示分歧、冲突、对抗不存在,它在。作为历史学者,我强调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权也无法改变历史。那么,历史学者最大的任务就是要真实、客观地还原历史,恢复历史记忆,从历史里面吸取各种经验、教训。
过去太强调冲突、对抗,太强调外交、政治、军事,很少有人从共有历史谈文化交往,所以这并不是理想主义,不是说这就是未来。但是,如果说分歧、冲突、对抗是一面,历史还有另一面,就是合作、共有。未来是不可定的,取决于我们当下怎么把握。那么,从历史吸取教训可能是最好选择。
我的主要诉求是强调历史的另一面,共有的历史、文化交流的一面。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但他们有多少人意识到贸易在中美两国之间是近 30 年的事?从美国早期立国一直到 1978 年,贸易经济关系从来不是重要方面,中国在美国国际贸易里面占的比例从来不超过 2% 。中美经济贸易问题变成问题,实际上是近几年的事。
我们现在纠结于贸易摩擦。所谓冲突、对抗,这是近几年,前面大多数都是求同存异。像“文革”时,尼克松来了,毛泽东跟他们搞乒乓外交,中美全面大和解。那时中美两国走到一起是因为有共同敌人——苏联。当然,邓小平改革开放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去访美。
所以,我强调中美关系史有另外一层历史。如果我们全面理解中国人与美国人历史关系的共有篇章,可以跟未来合作,可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有广泛历史借鉴,但并不表示分歧、对抗不存在。如果我们不吸取教训,或者吸取了错误教训,可能变成更危险。经常有人说入江昭教授太理想主义,倒是没有人说我理想主义。因为我写了三本书是关于战争的。我还写了一本体育的书。你知道奥威尔怎么定义体育吗?他说体育是一场不射子弹的战争(War Minus the Shooting),所以也是一种战争。

Q:现在关于“新冷战”的说法层出不穷,那你觉得中美未来会进入所谓的“新冷战”吗?
徐:所谓“新冷战”是个伪课题。“新冷战”表示有“老冷战”,“老冷战”就是美苏。美苏之间是零和游戏,非此即彼,所以美国人铆足了劲要把苏联人打下去。中美关系今天不是零和游戏。举个例子,如果中国经济崩溃,美国人也跟着受罪。如果中国留学生都从美国回来,美国好多大学基本上会关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没有这么多合作。另外,在许多问题上,中美需要合作,比方像朝鲜半岛、环境问题、打击恐怖分子问题、科技方面。
中美两国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按照希拉里的说法,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对中美关系抱有乐观,但是不乐观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如果它真把你从意识形态作为敌人,变成对手,回到当年要把苏联搞垮一样,不共戴天、势不两立。这就不可逆转,走了不归路,中国就有问题了。
我认为这是历史给中国最好的机会,我们要抓住。从 1979 年到现在,中国享受着和平红利。你现在不想和,不想平了,那就麻烦了。我们有时候有点自我膨胀,认为我们经济大了,国家强大了,但是你到乡下去看看,你看看我们的医疗,看看好多不公平的地方,距离很大,要做的事很多。你何苦再树个敌人?况且美国一直也不想把你当敌人,你让他毫无选择,他就跟你背水一战。
所以,第一,我不鼓励“新冷战”说,这是伪命题。第二,是不是真的进入“新冷战”?中国人自己有很大发言权,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你要选择,那么结果很难说。美国人这么多年,实际上没怎么变过。

中国到底是一个文明,还是一个国家?
Q:刚提到中国也面临严重的认同危机,你在书中说:“当中国人在 20 世纪初期丢弃儒家文化转向西方文明之后,又不得不陷入另外的怀疑:中国到底是一个文明,还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政党国家,还是一个文明废墟?……今天的中国继承了过去的遗产,却想以消化不良的外来体系为基础,拼凑出一个新的国家认同。”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也是你下一本书会处理的话题,所以看你能不能展开讲讲?
徐:前面我们一直围绕着中国的国家认同在谈。 100 年以前,我们寻找德先生、赛先生。 1895 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人要从文明变成民族国家。 1895 年以前,中国人常常认为自己是文明,不是民族国家。但是 1895 年之后,我们说不行了,要加入西方,想变成共和国、民族国家。国民党那时是党天下,现在也是党天下,不是民族国家,尤其现在很明确,党领导一切。所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什么呢?儒家文明吗?还是闭关锁国?我们现在有答案吗?我们接下来究竟往前怎么走?
现在这样明显有很多问题,那么要改。怎么改?所以我们现在面临比美国更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亨廷顿在临死之前写了《我们是谁?》,中国人更应该问问,何为中国?什么是中国人?这是个大问题。我目前正写一本书,书名叫 Idea of China 。全面梳理所谓中国的概念,从海外、从共有的历史谈中国。
Q:你愿意讲下你的核心观点吗?
徐:核心观点很简单。中国作为 idea 这个概念是单数,是中国人跟外国人缔造出来的东西。 1912 年以前,中国没有任何民族国家象征,没有国号。中国成为中国的正式名称是 1912 年,叫中华民国。在之前,你说我是中国人吗?还是说我是安徽人?过去大明大清,只有到近代,西方人把门打开了,你才要进入国际社会,所以我是从共有的历史这个角度(探讨)。这是我“共有的历史三部曲”最后一本,就讲这个概念怎么来的,里面涉及西方人、中国人,所以写的难度非常大。
Q:在新版《中国与大战》的序言中,你提到今年 6 月国际学术界会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巴黎和会 100 周年的意义和遗产。你也应邀出任会议国际筹备委员会委员。那你能否介绍现在国际学术界对巴黎和会有些什么重要讨论?你自己怎么看待巴黎和会的意义和遗产?
徐:巴黎和会的遗产跟五四运动的遗产,跟中外关系的好多遗产是连在一起的。我写了《亚洲与大战》,巴黎和会整个重新缔造了亚洲。不仅是中国,对亚洲国家来说,这方面研究极其薄弱。因为我是参加所谓的科学委员会,决定最后谁的论文能被入选,谁能参加这个会议。非常可惜,亚洲学者极少,应该没有真正中国本土的学者被选上。我也不参加,因为我马上就躲起来,要写 Idea of China 这本书。
对中国来说,巴黎和会跟五四运动连在一起。实际上,中国人历来有个错误,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了。我历来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根本没有失败,况且是成功了。中国人第一次借助最高级的国际舞台,把中国人的追求、梦想、想法说出去了。其中,顾维钧作为全权代表、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有好多人,还有留学生、工人团体都参与其中。当时顾维钧在外交舞台上,日本人没法跟他抗衡。顾维钧用的概念是西方的概念,是全世界、人类共同体的概念,自由、平等、公义都在他的口中,而日本人追求的是秘密外交、所谓强权即公理。中国在道义上战胜了日本,从而迫使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处于道德的被告席上,并因此在 1921 年华盛顿会议上,只好归还山东。
值此巴黎和会 100 周年之际,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反思巴黎和会百年的遗产。如果我们今年不好好反思一下,尤其把五四、巴黎和会、中美关系几个关键问题都放在一起加以详细分析,我们实际上很难走出现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
题图为清代留美中国学生组成的棒球队,哈特福德, 1878 年(华盛顿大学图书馆);长题图为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他的中国助手志刚、孙家谷(哈佛大学图书馆特藏)。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