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播女孩重度依赖:药物、网络与感情的三重过量
source link: https://blog.drawoceans.com/acgmn/582/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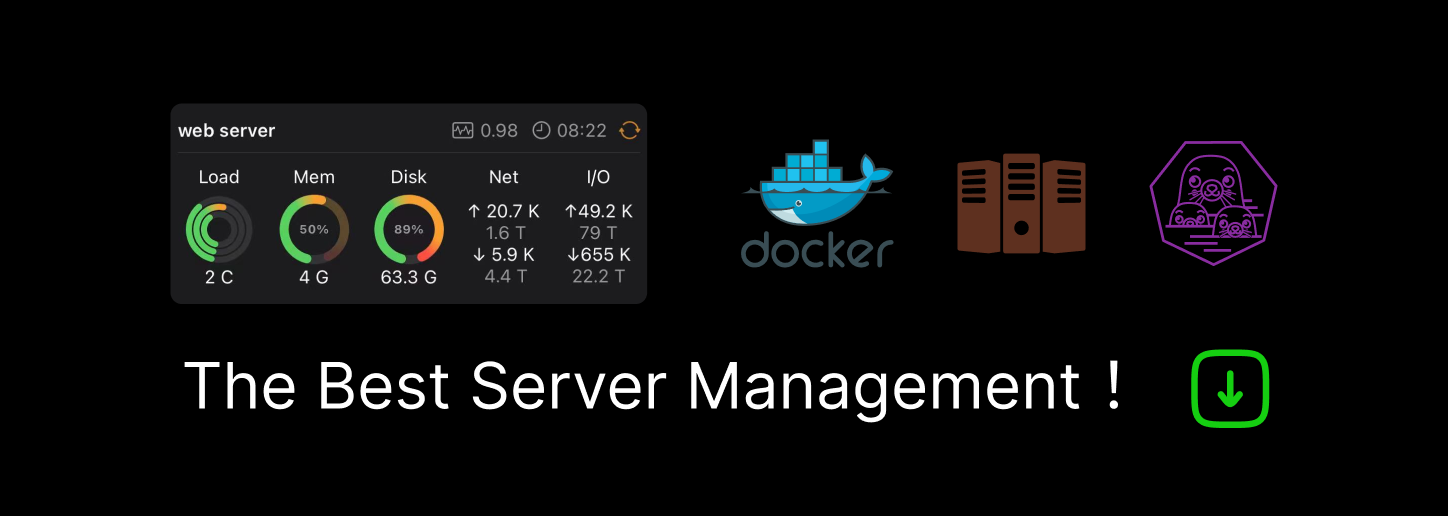
阅读提示:本文完全基于个人的独断与偏见,长约 18000 字,且包含大量剧透,请酌情选择是否阅读。
另外,玩游戏之前记得先和可爱的当代互联网小天使拉勾勾。
玩了3天,除了只能拼概率刷出来的 Megaten 成就以外都拿到了,游戏也打出了 Comment te dire adieu 结局(TE),除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还留有不少供具有收集癖的玩家们进行 CG 回收的小分支以外,游戏也可以算是接近100%完成了。趁着刚玩完还沉浸在余韵里的时候,来评价一下这款游戏吧。
(谁能想到我从1月29号鸽到了现在呢)
从结局开始
游戏的主题曲《INTERNET OVERDOSE》里有一句歌词:“おかしくなりそうなほど情報過多のインターネット(让人发疯一般信息爆炸的互联网)”,但是打完游戏之后,我感觉让人发疯和信息爆炸的不仅是网络,还有这个游戏本身。我在动笔写这篇评论之前,先到 steam 和b站上面看了不少别人给这个游戏写的评论。令我意外的是,有不少评论都提到了“讽刺”,认为作者一定是在讽刺如今这个荒诞的互联网世界,或者至少也是要讽刺已经畸形的直播文化。且不论这种现象与国内中学语文教学对“揣测作者创作意图”的追求之间究竟有多大关联,我觉得除了 TE 以外的每个结局最后会弹框一句话表达作者本人对这个结局的评价之外,作者的主观情感在这部游戏里表现得相当克制。实际上,虽然作者にゃるら在推特上的致辞中提到超天酱是作者自己美少女游戏中毒之后为自己创作出的完美女主角,但在作为玩家,或者剧本“读者”的我看来,这部游戏只是站在近乎中立的立场上,借助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糖糖”的视角既夸张又简化地展示了后现代互联网社会的荒诞图景。虽然有一些评论认为,作者在鼓励“糖糖”及屏幕前的玩家离开互联网回归现实生活,主要体现在 Healthy Party 结局、(Un)happy End World 结局、Labor is evil 结局和 INTERNET OVERDOSE 结局之间的对比上,以及 Happy End World 结局的名字和描述中包含的暗示(Happy End:“快远离因特网”),还有游戏开头画面右上角“INTERNET YAMERO”的 meme。但是,这些结局的最后无一例外都是 GAME OVER 的蓝屏界面,而没有蓝屏的 TE 结局 Comment te dire adieu 里,不依赖阿P,只借助自己力量的糖糖成为了 200 万粉丝的大物主播。但是,她离开了这个阿P,要“自己去抓住未来”,但是她离开了互联网吗?游戏里没有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不过,结合最终的“秘密.txt”里糖糖还要继续创造下一个“阿P”来看,恐怕不仅没有彻底离开“阿P”这种幻想男友的存在,也没有离开互联网吧。
真是一个悲观主义宿命论的结局。
超天酱提醒您:少玩网,多考证
这个游戏的各个结局,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 BE, GE, HE 和 TE 等等的划分。普通的恋爱 ADV 游戏,这些不同结局的区分是十分明显的:悲剧性结局一般就是 BE,主人公没有经历任何恋情则也是 BE 或者 NE,回避了悲剧性结局一般叫做 GE,与任一角色进入恋爱线路直至终局就是 HE,而与官方钦定主角经历重重冒险最终喜结连理就是 TE。但如果以这种视角观照这款游戏,能发现的只有绝望:哪个结局不是悲剧性的?就连看起来最积极乐观向上、靠自己的力量去抓住未来的 TE 里,最终也只不过是对这个“阿P”不满意,还要继续创造出下一个“阿P”。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来讲,对哪个结局是 BE、哪个结局是 HE 等等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每个结局都是 BE,就连在形式上最像是普通 ADV 的 TE 的 Comment te dire adieu 结局,虽然我也叫它 TE,但是这个结局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制作组在多个结局里钦定的真结局 True End,而是为了揭示这个游戏的真相所设置的 Truth End ——没有从痛苦的轮回中真正解放的结局,不也是悲剧吗?
现在,问题来到了这里:为什么糖糖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其结局和命运都是悲剧?一种看似直观的答案是,因为糖糖的双相情感障碍本身没有在当主播这个过程中真正得到治愈,就像齐泽克讲的“无限制消费”的笑话[1]一样:为了解决问题而采取的行动却加重了问题本身。不过,如果持续就医将阴暗度降至0,糖糖就会放弃网络回去考证,进入 Healthy Party 结局。然而这一结局同样是蓝屏 GAME OVER 的 BE,作者的弹框评价是“于生存而言,精神负担也是必要的”。这个结局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显得匪夷所思:难道看医生治好了病,从而放弃沉迷网络、回归现实社会,不应该是对糖糖而言最好的结局吗?但是,这其中被遮蔽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在游玩的过程中认真观察了各个选项的效果的话,会发现刷推博、自搜、看论坛、嗑药甚至色色都有可能增加阴暗度,而去一次医院只能减 10 点阴暗度。在通关 TE 之后我们知道,阿P只是糖糖幻想出来的人格,即使因为一时的行为暂时压制住了阴暗度,也随时有可能因为其它诱因再次陷入阴暗,甚至走上飞叶子舔“邮票”的道路,而这时的糖糖已经没有了“阿P”或者“超天酱”这些作为自我疗愈手段的退路——有意思的是,这种设定与现实中的心理和精神治疗中的情景很像:大部分治疗手段只能压制症状,而难以根治症状,导致精神疾病往往因为外界环境的诱因而好好坏坏、反反复复。甚至有一种常见于青少年心理干预的现象是,心理医生用尽了浑身解数去治愈,却敌不过患者家人一句漫不经心的话所带来的创伤。
现在,终于来到了这款游戏“让人发疯”且“信息爆炸”的地方:糖糖的双相情感障碍究竟从何而来?又为何无法治愈?这一问题过于宏大、与整个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而我显然没那个水平去回答。思前想后,还是从游戏标题到内容都反复强调的“overdose(过量)”入手,随便胡扯几句好了。
参观人造天堂的天使
大麻和罂粟作为植物存在于地球上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还要长,但被制成现代意义上的毒品以供吸食距今不过两个多世纪。不过有一个可能令当代人震惊的事实是,鸦片,甚至后来出现的更加强力的毒品海洛因,最早居然是作为药品开发和销售的。事实上,用罂粟提取物作为原料的阿片类药物,至今仍是人类所掌握的最强力的镇痛剂,通常用于缓解分娩或者癌症引发的剧痛。甚至,一些强力感冒药和止咳水中也可能含有微量的可待因和咖啡因等成瘾性物质——海洛因治咳嗽不仅是个历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笑话,它现在仍然活生生地发生在现实当中。而随着弗洛伊德第一次用科学的眼光(虽然在实证主义的角度上可能也不那么科学)审视人的心理世界,疯狂成为了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症状,各种抑制精神症状的药物和疗法也相继问世。但是,这二者的相遇,却带来了全新的公共卫生问题,并逐渐威胁整个世界——物质滥用和药物过量,而游戏的主人公糖糖显然精于此道。
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玩家们都没有亲自参观过人造天堂——有的话请立即到最近的派出所自首。因此,玩家实际上只能通过游戏的演出来感受主人公糖糖症状发作以及嗑药时的体验。虽然我一直坚持文本中心论,比较抗拒在评论时去关注作者本人,不过哪怕排除了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的对毒电波系游戏,尤其是《对你说再见》这部经典毒电波作品的狂热以外,这部游戏的主题曲 PV 中反复出现“poison radio”、“毒电波”等关键词,以及有相当一部分时长都在致敬《对你说再见》、《雫》、《终之空》等著名毒电波作品,游戏内容中也出现了这些作品的 neta,甚至游戏的最终结局名字 Comment te dire adieu 就是《对你说再见》的副标题。所谓“毒电波”,就是汉语里的“脑控”,指用电磁波控制人脑的行为——当然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只不过是精神病人的妄想而已。因此,虽然不是每部作品都以脑控为主题,但描写精神病人及其妄想世界的作品基本都算毒电波系作品。
出于这种题材特点,我认为毒电波系作品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如何让身为普通人的玩家体验到作为精神病患者的主角的感受,换句话说,就是感受到那种“狂気(疯狂)”。不过,这种疯狂在没发疯的玩家看来,通常显得比较怪诞和恐怖,虽然毒电波游戏往往有别于恐怖游戏——恐怖游戏以提供惊吓和恐怖为主要目的,而毒电波作品的恐怖则是展现疯狂的副产物。话虽这么说,我这个玩不来恐怖游戏的人对毒电波作品一般也都是敬而远之的:只玩过《素晴日》,《对你说再见》等游戏虽然久闻大名——可能要归功于我有一个喜欢毒电波游戏的朋友——但即使好多年过去都不敢实际去玩一玩。不过有意思的是,一般被视为毒电波系开山之作的《雫》,其灵感来源一般认为是大槻健次的小说《新興宗教オモイデ教》[2]。从小说到文字 ADV 游戏可以说是一种飞跃:相较于只能借助文字的小说,文字 ADV 游戏还可以借助图像、音乐、念白、音效、视觉效果等多媒体手段提供体验。虽然视频也具有以上特点,但是文字 ADV 作为一种游戏还具有游戏独有的互动性:不同于读者被动的线性阅读和接受,玩家会因为自己的行动看到不同的故事走向。可以说,在 2000 年前后的日本出现的这一批毒电波系游戏,在观念和形式上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资源可供发掘——例如,很难否定 LeaF 的那些音乐作品及其 BGA 没有受到过这些资源的影响。
不过,这部游戏的主题还是侧重于“当主播”,而不是“看糖糖发疯”——总的来说,不太算是毒电波作品,所以这些毒电波系的演出只有在压力值爆表引起症状发作时,或者嗑药时才会出现。在我看来,本作中的毒电波演出和那些经典的毒电波作品中的演出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你可以很轻松地读懂这些演出的象征意义。毒电波作品,通常侧重于通过精神病人——通常是重型精神疾病,比如会造成妄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扭曲、变形了的视角进行叙事,总而言之,是通过叙述和演出效果营造出不同于常人的陌生和疏离感,进而实现某种叙事目的。而本作的毒电波演出几乎是一望即知的,比如在高压力(大于80)时会桌面会从淡粉红变成红色并触发割腕事件,而压力值第一次爆表、压力上限提升之后画面会歪斜,虽然游戏画面模拟的是一台 CRT 显示器的屏幕,这里可以看作是糖糖发作后砸歪了显示器,但也暗示了糖糖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下所看到的世界。再比如嗑药的时候屏幕会出现噪点并扭曲,游戏 BGM 也会相应出现变化,试图向玩家再现嗑药时糖糖的主观感受。NEEDY GIRL OVERDOSE 结局中,面对最后的问题,屏幕画面会变得不稳定并逐渐变红,两边也会出现波形特效,既暗示着可能到来的悲剧性结局,也配合结尾 N 连问给玩家带来不少压抑与紧张感。而最阴间的还要数 INTERNET OVERDOSE 结局——这应该是整个游戏里毒电波演出最多的路线——无论是糖糖把本来正常的文字误认为乱码,还是把匿名论坛上的留言看成是一只只透过屏幕注视并嘲笑她的眼睛,以及与“阿P”的对话里出现了各种支离破碎的妄想画面,都是精神症状进一步恶化、失去对世界的正常认知的表现。顺便一提,在我看来这种展现精神病人的妄想的演出,才是最纯正的毒电波演出。
我必须承认,我对于现代精神病学存在着相当大的偏见。这种偏见不仅仅是福柯式的对“何为精神病”这一划分标准的怀疑,更是因为现代精神病学的治疗手段处处体现着一种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它将人脑视为一部有机的机器,而疯狂则是机器的运转出现问题的表现,只要通过物理的或化学的方法加以调节,就可以解决问题并消除疯狂,精神病也就治愈了。不过,必须要承认的还有一点,即无论福柯的怀疑正确与否,精神病患者的痛苦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这种机械调节的手段是消除痛苦最快的方法。然而,最快的就是最好的吗?当睡眠、快乐、安心感都需要药物来代替人脑本身的生化反应提供时,对精神类药物甚至毒品的依赖和过量使用就已经成为了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为了压制症状而给药,但症状却随时有加重的可能,不得不给与更大的剂量来压制更严重的症状,治疗在这里陷入了死循环。
但是,医学的经验在此发挥了作用:如今的精神病治疗,哪怕只有这些压制症状的手段可用,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症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视就医时机和依从性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患者往往不愿前往医院接受正规治疗?幸运的是,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精神类疾病的医疗资源在当下依然十分紧缺,再加上治疗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是大多数患者难以承受的。其次,精神类疾病的治疗还需要很高的依从性——不如想想你自己平时吃感冒药的时候有没有为了追求尽快康复而一次吃两片的时候,这也算是不遵医嘱以及药物过量,虽然往往不会成瘾。此外,精神疾病带来的病耻感也是许多已经自觉症状的病人不愿就医的理由。 令人欣慰的是,如何让心理和精神类疾病患者更容易获取医疗资源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相信这一问题终究会得到改善。
不过,在这一问题还没得到改善的现在,最恐怖的不是“精神病治疗只有压制症状的手段可用”,也不是“精神病人难以得到正规治疗”,而是“精神病人得知了精神类药物的存在却难以得到正规治疗”,换句话说,是在没有专业精神科医生指导下的私自用药,这才是在精神类疾病患者间物质滥用和药物过量行为高发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失去了医学经验的支持的情况下,从滥用含成瘾性成分的感冒药和止咳水开始,再到各种精神类药物,甚至最后演变成吸毒也不是不可能——游戏里的药物种类会随着阴暗度的提高而增加,现在想来似乎就是顺着这个路线进行的。但是,药物过量不是一个只在精神病患者群体内发生的行为。在一些关于青少年药物过量行为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描述:当事人往往是因为某种与精神症状无关的原因——甚至可能单纯是因为治疗咳嗽接触到了含有成瘾性成分的药物,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此外,因重大打击或变故走上物质滥用和吸毒道路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虽然从大麻和鸦片初登场的 19 世纪起,就有不少艺术家,包括画家、诗人、音乐家等,主动吸食毒品,以在这种“人造天堂”中经历从未有过的体验,寻求全新的创作灵感。这些人留下了不少关于吸毒体验的文字记录,如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还有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柯勒律治也对吸毒后的体验发表过不少感受。甚至在现在,仍然有艺术家相信毒品可以带来新奇体验和创作灵感——看看在美国说唱歌手群体中大麻的吸食有多普遍就明白了。然而,一些评论家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
根据现代医学的临床报告,在这些吸鸦片的诗人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异常成分,看来是来自他们神经质的心理,而不是来自麻醉药的特殊功效。施奈德(E. Schneider)告诉我们,德·昆西的“文学上的‘鸦片梦’,虽说对后来的著作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除了精细一点外,与他 1803 年未吸鸦片前所写的一则日记并没有多大不同”。[3]
但是,那些并非从事创作性工作——甚至有可能不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们,到底为何选择去打开人造天堂的大门呢?恐怕还是要回到那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论调:药物可以强制性接管人脑的生化反应,为服用者带来哪怕是虚假的快乐、幸福和睡眠,以掩盖精神上的痛苦。失眠和精神痛苦并非精神病人的专利,尽管现代的精神病院也同样进行神经症的治疗,但或许是因为路径依赖,他们同样会向没有器质性病变的神经症患者提供这些药物,虽然一般来讲是相较而言药效不强的那种。至此,一个悲观的图景显现在我们眼前:一个精神痛苦的人实在是太容易接触乃至滥用这些药物以无限制地参观人造天堂了。不过术业有专攻,在这里我们还是暂时相信专家们的力量,把“如何让更多人得到正规的心理和精神医疗资源”的问题交给社会学家,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范式转换问题交给那些专门的研究者。然而,在我看来,这些不过是权宜之计,是给四处漏风的危房糊上木板,终究还是免不了坍塌的命运。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什么造成了这么多人的痛苦?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快乐、睡眠和幸福感,甚至只能依赖于药物?
不再是工具的网络
相较于 19 世纪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的相继发明,整个 20 世纪前半仿佛陷入了沉默。但是,正是因为短短半个世纪内接连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大量且快速的计算的需要,催生了计算机这一划时代的发明。接着,在已有的电报和电话的成就之上,诞生了在计算机之间交换信息的伟大造物:互联网。是的,就像是看似无所不能的现代计算机实际也只是利用晶体管进行数学运算,和它巨大、缓慢且难以使用的老前辈 ENIAC 在原理上没什么太大区别一样,互联网这一能在一秒内连接全世界的伟大造物,实际上能做的就是和电报一样,通过电线或者电磁波在两台电报机或计算机之间传输信息——今天的互联网依然在忠实地执行这一任务,甚至或许执行得太好了,让人产生了世界不在自己身边、反而在屏幕背后的错觉。如果说电报收发不易使它成了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电报员才能操作的复杂机器,可以直接对话的电话则依然没能克服只能一对一通讯的缺点,而互联网在这方面则是开创性的——服务器与客户端的二分,第一次实现了一对多的直接通信,就像我们可以在现实里做的那样。
我大概是在 2004 年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那时的我甚至还是个没上小学的小屁孩,直到 2010 年我才离开 Flash 小游戏的世界,算是真正开始了上网冲浪,至今已经 11 年有余了。唯一可以断定的是,彼时的互联网和如今的互联网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任何技术的发展,几乎总是伴随着廉价化:电话和电视的价格在它们刚刚投入民用市场时都奇高无比,个人电脑和家用网络也是如此。在 90 年代,一台个人电脑要花去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几年的收入,更不要说奇高的网络资费。而现在,一台同样能连接到互联网的智能手机,最便宜的只需几百元;网络资费也大幅下降,即使是相对昂贵的移动网络,一个月的价钱甚至还没超过一顿洋快餐。如今的网络速度也早就不可与当时同日而语:90 年代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时,广泛采用的上网方式是通过电话线传输的拨号网络,而那时的理论速度上限甚至还不到后来的 56kbps,而是 14.4kbps——千比特每秒,换算成今天的我们更熟悉的网速单位 MB/S 大概是 1.76MB/S。看起来不错,然而这只是个理论上限,就像如今的光纤网络的理论速度上限可达 10Tb/s 一样——实际用起来速度基本上只有每秒几个字节。
不过,昂贵的价格与极慢的速度却造就了互联网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昂贵的价格使得能在那时接触到互联网的人,要么是出于工作需要才能接触到如此高端的科技产物,要么是家境殷实、足以买得起一台可以称得上是奢侈品的个人电脑。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往往都与高教育水平和高素质成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极慢的速度使得网络上只能传递简单的信息,而不可能像今天一样信息爆炸。彼时的互联网,作为一扇“新世界的大门”,那些得以接触它的人们对这扇门及其背后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也对自己在新世界的同行者们抱以友善和尊重。不过,世外桃源不可能永远都是桃源。随着互联网变得廉价而普及,这个曾经遗世独立的小世界急速扩大、充斥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与我们身处的现实越来越相似。然而,互联网即使与现实再相似,有一个自其诞生以来的特点却到现在也没被颠覆:匿名性。如果只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几乎不可能在广泛使用 NAT 和动态 IP 分配技术的家用网络条件下追查到一台发送信息的主机——简单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网络使用者,想要只通过技术手段知道另一个网络使用者到底是“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句非常有名但找不到出处的互联网名言警句的原理:在网上,甚至没人知道你是不是一条狗。然而,有一种使用者众多的互联网服务,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技术上的匿名性,使得网络与现实开始逐渐混合:社交网络服务,简称 SNS。
SNSという瓶詰地獄に救済を
给名为 SNS 的瓶装地狱以救赎——游戏主题曲《INTERNET OVERDOSE》歌词
虽然我觉得这游戏的主题曲的歌词里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句子,但这一句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我不知道是作者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将 SNS 比作“瓶装地狱”的这个比喻简直精妙绝伦。把这个偏正短语拆开来,SNS 首先是“地狱”,然后才是“瓶装的地狱”,为什么这么说?SNS 诞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让人能通过网络与自己的朋友交流,在这一点上,和以前与朋友写信、打电话等交流方式别无二致。但是,SNS 与那些老古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信和电话不会知道你都有什么朋友,但 SNS 知道,而且为了能让你长时间使用 SNS 服务以便让服务商从中盈利(比如长时间观看广告),它还会试图让你认识你“有可能感兴趣的人”,比如推荐你朋友的朋友给你认识。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问题:书信只能传递文字,电话只能传递声音,而网络可以传递一切多媒体信息;推荐机制还能帮你扩大社交圈子,和你的朋友们保持同步。确实,SNS 刚刚诞生的那个遥远年代,它的确是这么工作的:还有人记得人人网还叫校内网的那个时代吗?彼时的校内网几乎是大学生实名网络交友平台,因为在那个个人电脑依然昂贵的时代,大学生却可以通过学校机房和校园网方便地访问网络。换句话说,彼时的 SNS 还是让你更方便地和朋友保持联络并发现新朋友的工具,还是为你的现实人际关系服务的。
但是,一个用户在 SNS 中发布的内容往往是碎片化的:几行文字、几张照片或者一小段音视频——而且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还会因为 SNS 自身的社交属性而公开,甚至被推荐算法广而告之。这就导致通过 SNS 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只能接触到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去想象ta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总而言之,一个人通过 SNS 展现出的自我是碎片化的。问题正诞生于此: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左右自己发布的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来操纵其他用户对自己的印象——换个更加简炼的说法,立人设——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甚至,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任何一个人完全可以以一个虚拟的身份加入 SNS,这时又会发生什么?最直观的答案是,这些“人”是一些只存在于 SNS 社群的“用户”,而其他人通过这些信息在脑内补全的那个本应存在的现实世界中与之对应的“人”则完全不存在,尽管这个“用户”一定是某个人扮演的。SNS 服务的本意是作为让用户通过互联网与朋友保持联络并发现新朋友的工具,但因为这种匿名性,完全可以从中几乎零成本地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人,在这一刻,SNS 社群与现实人际社群之间的一致性被打破,SNS 创造出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社群的虚拟社群。如果说“糖糖&超天酱”这种真人出镜的网络主播对这一点体现得还不够充分——毕竟超天酱可以去探望她的小女孩粉丝——那么不能从屏幕里走出来的 Vtuber 则是目前为止这种虚拟性的最高体现。
不难想象,扮演这些用户的人——暂且不讨论他们为什么要扮演——每天都会做些什么:为更好地扮演“用户”收集素材,因为这种扮演行为乃是通过碎片信息的发布所维持的。在游戏中就体现为,糖糖要为了凑直播素材做出各种行动,甚至连色色也能为直播提供灵感。与之类似的是,不知现在是否还有人记得 2020 年 10 月有一篇名为《我潜伏上海“名媛”群,做了半个月的名媛观察者》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火遍全网,荒诞的事实背后折射的是相同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是为了扮演网络上的“用户”取材,这些人就这样成为了活在 SNS 所构建出的虚拟社会里的人。用最简洁的话来说,不是人上网,而是网上人——网络与人的关系不幸发生了颠倒。对这些网络社会的居民来说,社交网络不再是那个用来和现实朋友保持联系的工具,而成为了 cosplay 的场所。乍一看,人仍然具有主动权,但每个人每天公平地只拥有 24 小时,如果这种 cosplay 行为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人就不得不把时间从别的行动中抽走,而 SNS 和网络虚拟社会则在人们的 cosplay 中强化着自身,让人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在网上打造“人设”、扮演“用户”,而这个网络虚拟社会正是通过他们的行为维持着自身的存在。这样,人就成为了网络虚拟社会存在及强化自身的手段。
或许有人要反驳说,我不当网红,也不立人设,自然不会去玩这些赛博 cosplay,怎么还会被网给上了呢?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如今的 SNS 大量应用的一种伟大而邪恶的发明:推荐算法。发明推荐算法的本意,是为了让你更方便地找到可能与你成为朋友的人:比如有相同的朋友或者爱好。所以,它有可能把你朋友的朋友推荐给你,或者给你推荐与你听了同一首歌、读了同一本书、看了同一部电影的人——总之,一定在某一点上与你相似。虽然现实中扩大社交圈的逻辑与此基本一致,但计算机和互联网总是象征着高效,或许甚至有点过于高效了:在它的作用下,会筛选出大量与你拥有相同观点的人和内容,而你甚至没有看到那些不同观点的机会,使得你总是看到你想看到的信息,并且认为自己才是大多数——这就是老生常谈的“信息茧房”、“回音壁效应”和“同温层社交”问题。由此,意见的对立形成了立场的分歧,而在推荐算法的作用下,你该 cosplay 的角色已经准备好了,哪怕你觉得你没在 cosplay。如果把这一点与之前讨论的匿名性加以结合,事情会变得更加恐怖:匿名意味着难以定位到用户背后的人,换句话说,难以对网络言论追责,而这只会使网络言论愈发肆无忌惮:从讨论到争吵、再到互相谩骂往往只在一瞬间,甚至还可以直接跳过前两个阶段。作为结果,曾经的世外桃源现在满是戾气,一颗小火星就能引爆整个火药桶。
这种只是窥视一眼就很有可能陷入其中的深渊还真是个地狱,或者应该说更像是拉莱耶。不过,这还只是“地狱”的部分。瓶子看起来在人类历史的极早期就出现了,因为这东西制作起来实在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细且高、不漏水、能封口的容器都可以是瓶子,无论是用陶瓷、木头,还是金属、玻璃,或者是现代的塑料,造个瓶子都属于最简单的技术。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语境下提到“瓶装”,我猜你多半会想到在超市里摆成排的塑料瓶、玻璃瓶或者易拉罐装的各种酒水饮料。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瓶装饮用水”这东西相当有意思,不仅仅是花一两块钱就能买到实验室级别的纯净水,更是因为,水本来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生物的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东西,一旦装进塑料瓶、摆到货架上,就成了一种商品。而且,你在同一品牌的两瓶饮用水之间通常发现不了任何差别,即使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去分析,也只有极其细微的差异。总而言之,水这种自然资源经历了“瓶装”之后,成为了一种标准化的商品。如此看来,SNS 的确可以看作一种“标准化”的商品,毕竟 SNS 是一种公司提供的商业性服务,而且说实话每个 SNS 的功能都大同小异。但是反过来,SNS 的用户是否也是一种被“瓶装”了的商品呢?或许不是,可能还不如商品。尽管现在的互联网看起来热闹非凡,处处都是战场,但是只要多看几个不同 SNS 网站,就会发现大家好像都在讨论同样的话题、输出同样的观点——这很好理解,毕竟网络虚拟社会不和某个网站绑定,既然一个虚拟人格可以使用这个 SNS 网站,就没理由不能使用那个 SNS 网站。但细思极恐的是,这些虚拟人格,岂不是被网络虚拟社会“标准化”地生产出来,然后流入各个 SNS 网站的吗?而 SNS 又要通过这些“用户”来盈利——它们可能不太在意这些“用户”到底是一个利用 SNS 与朋友保持联络的原教旨 SNS 使用者,还是利用 SNS 打造人设的网红或交际花,又或者是被裹挟着参与大型网络 cosplay 的普通人。说到底,只要是自己的“用户”,就可以为自己牟利:SNS 是公司的私有土地,“用户”则是在上面耕作、为公司赚钱的角色,而且由于连账号这一“用户”得以存在的基础的生杀大权都由公司完全掌握,因此“用户”与其说是租用“土地”的“佃农”,不如说是依附于公司的“农奴”——一种赛博封建制。
拔网线,保平安
然而,我们现在真的拔得掉网线吗?对于 80、90 后来说,网络是在他们35岁前诞生的改变世界的新技术;对于 00、10 后来说,网络则是他们出生之前就存在的世界的一部分。如果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科技三定律[4]还生效的话,那些年龄更大的人似乎不太会去接触互联网,但事实恰恰相反。4、50 岁的中年人熟练使用互联网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但当我见到自己 70 多岁的姥爷熟练地用智能机网购、缴费、刷快手的时候,我的确得承认我的世界观被刷新了。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老年人愿不愿意学或者学不学得会上网,而是这个游戏发售的时间。这游戏在 2021 年春发布了 PV,但是一直跳票到 2022 年年初才正式发售,这两年全球正在经历什么世界级事件想必我不说大家也很清楚——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出于预防感染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事情被“线上”取代了:网课、居家办公、线上会议……应该说,在这里我们本来应该感谢互联网这一技术,有了它我们才能有这些替代形式,不至于让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陷入完全停滞。但与之相对的,网络取代了越来越多的线下见面,换句话说,疫情给网络带来了机会,使它能更进一步入侵现实——网络已经日益成为一种新基础设施,就像道路、煤气、自来水和电力一样。换句话说,想要逃离网络,不如先想想自己能不能逃离道路、煤气、自来水和电力。
いいね よくないね キミにとっては毒だね
いいね よくないね それでも飲むんだね
赞 踩 对你来说是毒药
赞 踩 但还是喝下了——游戏主题曲《INTERNET OVERDOSE》歌词
但是,即使 SNS 已经成了这样一个“瓶装地狱”、“赛博封建庄园”,即使网络越来越重要,重要到位列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之一,SNS 终究只是基于互联网技术提供的一种服务,而不是网络的全部——尽管不能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访问网络主要就是在玩 SNS。而且,即使 SNS 是什么深渊、拉莱耶或者美杜莎的眼睛之类的,只要看一眼就为时已晚的东西,那起码也要有最初的那一眼。更何况上面讲的东西都是一些很浅显的朴素认识,想必各位长年上网冲浪的人多少也都体会到了。在游戏里,糖糖也发过这样的推博:我只能从互联网获得快乐,但互联网也会给予我等量的痛苦。那么,为什么明知网络是毒药——或许在刚刚接触的时候的确不知道——却仍有那么多人选择在网络上“痛并快乐着”,不停重复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难道真的因为是“人迟早都要死所以及时行乐”吗?或者是因为网络具有某种魔力?
找不到出口的感情
按理来说,这里应该来点精神分析,可惜我对精神分析的学习仍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说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况且我想应该也没什么人真的想看长篇累牍的哲学黑话,尤其是这黑话里还充满了什么“阳具”、“性欲”之类看起来就少儿不宜的东西。所以,我还是接着讲朴素认识好了。
放张精神分析 meme,就当我讲过了吧
如果你自己观察过糖糖对各种贴纸的回复和在加锁账号里的推文,就能发现存在反差:糖糖对“太强了”这张贴纸的回复通常是充满骄傲的,对“永远爱你”的回复也不吝于表现自己对“阿P”的爱意——但是在自己的推博里,糖糖发的却大多都是 emo 的内容。打通了 TE 之后我们知道,“阿P”实际上是糖糖的臆想,那么有意思的就来了:“阿P”是玩家的视角,那么“阿P”给糖糖发送的那些贴纸和消息,在故事里应该是糖糖自己给自己发送的,而糖糖对“阿P”表达的爱意,就应该是糖糖给自己表达的——那么,玩家到底是在以何种视角阅读这个故事?有些评论认为,玩家像戏剧里的观众一样,不在这个舞台之上,而在舞台外的座席上面。或者,至少像是 Rainbow Girl 结局一样,玩家是在游戏世界之外,干扰着游戏世界进程的“神”。不过,小说和戏剧不需要读者或者观众与其故事内容直接互动,但是游戏需要。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玩家的视角就是糖糖自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初入游戏的时候就察觉到了异样:一对同居的情侣为什么需要通过聊天软件和网络摄像头交流?为什么通过网络摄像头就能真的摸到糖糖的头?更何况,在 NEEDY GIRL OVERDOSE 结局中,如果你没能及时安抚好糖糖,她便会一刀剁了显示器,而黑色屏幕的反光中映出的则是糖糖自己的身影——这几乎是明示了坐在“屏幕”前面的人就是糖糖自己。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看待这种反差,就显得更有意思了:“阿P”是糖糖的幻想,连带着这个“女友”的地位也是幻想出来的——是不是可以说,糖糖在 LJNE 中作为女友与“阿P”互动时的表现,展现的实际上是糖糖对于“作为某人女友的理想的自己”的幻想?在游戏中可以看出,糖糖对自己的认识是“除了颜一无所有”,比如第 15 天必然触发的抑郁对话里,糖糖认为“超天酱”的粉丝们都是为了颜值才关注自己的。虽然你完全可以把那些对贴纸的回复看作是一些为了让游戏显得更真实的小细节,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这种细节?或者说这细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糖糖在和“阿P”的对话中,除了一以贯之的抑郁和 emo 以外,展现出了更多的爱和自信,然而这爱和自信是在幻想和扮演的基础上才有的,换句话说,它们属于糖糖理想的自己,而不属于糖糖本身。但是,面对“阿P”的那些爱和自信,或许也是糖糖给自己施加的心理暗示吧。在 Os-Alien 结局里,糖糖由于对“阿P”的满好感度而什么都不想做,只想沉溺于这种角色扮演中获得哪怕是虚假的爱。但是在 Angry Otaku Needy Girl 结局中,糖糖由于低好感而抛弃了“阿P”,选择加入大手 MCN 并成功和大物男主播交往。然而当糖糖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是大物男主播的玩物时怒发冲冠、一转打拳——说实话,我玩到这个突兀而荒诞的结局的时候几乎笑出声来。但是,这两个结局的对比是否暗示着糖糖对爱的需求只能通过这种幻想的方式实现?糖糖从宅文化产品中获得了“恋爱可以得到爱”这一认识,于是为了能进入恋爱便幻想出“阿P”这一必要的男友角色,一旦对“阿P”的幻想产生了动摇(低好感度),便会为了继续获得爱而进入真实的恋爱——但是心病且不善社交的糖糖进入到“恋爱”这种高难度亲密关系时会发生什么,Angry Otaku Needy Girl 结局已经给了我们荒诞却真实的答案。
与对“阿P”的爱相反,糖糖对自己的宅宅粉丝们好像没什么好感,似乎还有些厌恶。对宅群体的刻板印象想必不用我再复述了,“喜欢宅文化的美少女”这类角色也早就品鉴得足够多了,比如最经典的高坂桐乃,还有和泉纱雾——可能不是因为伏见司整不出别的活,而是死宅们的确就好这一口,但我还是要问一句伏见司你什么时候〇啊。但是,如果说到糖糖与这些角色之间的距离的话,只能说是因为糖糖没有处在一个充满了宅臭味的故事里吧:媚宅的故事是精心编织的一个梦,而这个游戏只是在展示一种现实的可能。说到这里,一般而言这种“喜欢宅文化的美少女”的角色,往往会把“宅文化”和“宅群体”分得非常清楚:她们喜欢的是“宅文化”,但排斥作为刻板印象的“宅群体”(说的干脆一点就是死宅),即使她们自己也是消费宅文化的宅群体的一部分。这里暂且不去探究这种现象的成因——毕竟我说了我不懂精神分析——而是说,在我看来这种矛盾才是这个游戏得以成立的基础。尽管糖糖讨厌这些动辄对她品头论足甚至直球性骚扰的死宅,但是糖糖的被承认欲最终还是由这些粉丝实现的,甚至连她的直播也是得益于她和死宅们共享的宅文化语境才得以实现(或者其实说得更加直白一点,难道深层原因不是利用了宅男们的性焦虑吗?)。这种“消费宅文化但讨厌与自己共同消费宅文化的死宅”、“利用性焦虑吸引宅男粉丝但讨厌发送直球性骚扰言论的宅男”的现象,似乎和波兰等保守主义抬头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如出一辙:反对 LGBT 等左翼议题而支持保守主义的女性们,等到保守主义禁止了她们的堕胎自由后,便神奇地全然忘记了自己先前的反对立场,转而支持左翼去了。当然,在我眼里,性骚扰言论和堕胎不自由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背后的逻辑竟然出奇地一致:你很难只要某个整体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你不得不接受它的全部,无论是宅男粉丝还是保守主义。不过,糖糖想要的终究还是被承认(如果你仔细看了糖糖在游戏一开始发送的消息),而不是宅男粉丝,宅男粉丝只是满足被承认欲的一种方式罢了——但这游戏的基础正在于这种错认,即将当主播赚粉丝作为唯一能获得承认感的手段。
被承认欲这东西,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说起来,在高好感高阴暗的条件下,有几率触发糖糖的抑郁小作文,讲述了糖糖过去遭遇校园霸凌、父母离婚、体弱多病、需求被无视和家庭贫困的经历。当然,你完全可以继续把这些当成是完善糖糖角色形象的小细节,但是这些细节与那些对贴纸的回复而言,显得更加能调动起玩家的同理心: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其中一些事件,至少也能对这些经历感同身受。说起来,有人说电波作是会挑读者/玩家的,只有那些对得上电波的人才会读/玩得下去,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任何作品都会挑受众。糖糖的这个形象,说实话在一些角度上让我想起了《春物》里的大老师:总有人读过几卷《春物》或者看了动画之后,就觉得大老师简直就是自己的写照。但是大老师和糖糖显然不是任何具体的人的写照,而是一类人形象的最大公约数,换句话说就是“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之所以能引起共鸣,要么是我们身边甚至自己就有着人物的影子,要么是我们与作品中的人物之间有着相似的经历——总是要有一种“共享经验”。不过《春物》毕竟是轻小说,朝着恋爱喜剧的方向一去不返了,因此我建议如果有人想代入《春物》,可能材木座比大老师更适合你。回到这个游戏,有些经历过家庭暴力或校园霸凌的人想起了自己,有些主播看到糖糖努力当主播的经历想起了自己,有些曾罹患精神疾病的人看到糖糖的表现想起了自己,而有些管人观众看到游戏里的主播与粉丝也想起了自己,还有些人没想起自己,而是想起了自己和糖糖一样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前男/女友——然后他们涌入所有和这部游戏有关联的地方:游戏的 steam 评论区、游戏的宣传片视频、主题曲的评论区、游戏的直播或录播现场,迫不及待地与别人一起确认这种共享经验。
不过总有些人什么都没想起来,或者他们没把这个游戏的故事当一回事——说实话这是好事,因为这个甜美的游戏背后隐藏起来的部分才是最沉重的。他们同样涌入了这些地方,然后像游戏里的粉丝一样到处发着“小天使请安”和“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5]
我一直都觉得,把宗教比作鸦片是一个绝妙的比喻:一方面,宗教和鸦片一样,给痛苦的人们提供麻醉和暂时的欢愉;另一方面,宗教和鸦片又是面对现实的痛苦走投无路的选择,真正重要的是,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么多人的痛苦?伴随着这个问题,三种过量最终走到了一起:因为痛苦,所以会主动去药物过量享受暂时的幸福;因为痛苦,所以会像中毒一样沉溺于唯一能获得快乐的网络而不可自拔;因为痛苦,所以会尽一切可能为内心堆积如山的痛苦和被爱的欲望寻找出口。因此,这部游戏留下的最终问题就是,糖糖,以及一切能与这部游戏有共感的人们,到底为什么如此痛苦?据说,自残是语言无法言说的痛苦得以表达的方式。糖糖压力值过大的时候,会触发割腕界面,让“阿P”,实际上也就是糖糖自己,不停地划自己的手腕。但是,嗑药不仅伤肝肾,药物的副作用甚至会带来更大的精神痛苦,而除了直播以外,不停在网上刷推博、自搜、看匿名版同样会给自己积攒压力和阴暗度——说到底都是自残,一种是物理上的自残,而另一种则是精神上的自残。说实话,我不知道这种痛苦的成因——你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万恶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但是资本主义是如何造成这种痛苦的?
即使只有石头可推
我在本文的写作途中时不时就会想起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虽然我只是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翻了翻而已,而且说实话,我不知道是德波的原文如此,还是国内译本的问题,读起来十分晦涩难懂,只能靠着张一兵和其他学者写的导读才能一窥此书之奥妙。当然可以说,这游戏展示出的问题已经被居伊·德波、鲍德里亚以及其他致力于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的学者们解释得非常清楚,就连我回答不出来而留在文章里的那些问题也已经由他们回答了。但是,我这种并非专业学者的普通人,即使通过阅读和学习知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新的问题又旋即诞生:知道了之后呢?有人说知识是一种诅咒:当你知道了“什么”之后,你就再也回不到不知道的那个状态了。会游泳的人再也不知道不会水的人为何在水中如此慌张、会骑自行车的人再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永远会从车上摔下来。尽管我近乎一无所知,但我经常觉得,或许比起我这种半吊子来说,那些真正一无所知的人活得更加幸福。
虚无主义及其造成的精神危机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休谟的怀疑论大概是最早揭示虚无主义的。或许唯一的不同在于,那个时代能注意到这种精神危机的人还不多,而现在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开始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在尼采看来,旧道德和旧宗教幻灭之后,虚无主义就诞生了——有点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景象。人不应该成为这种虚无主义的奴隶,更不应跟着社会上的大多数随波逐流,而是应该转向积极乐观的虚无主义,“重估一切价值”,勇于自我超越和突破,直至超越人类的丑恶和兽性,成为“超人”(Übermensch,不是 DC 那个 Superman)——但是这有些过于困难了,尼采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种超人,甚至我总觉得,超人是尼采提出来的一种极端美好的情况,用于反衬被虚假的道德和宗教以及虚无主义吞没的“末人”的悲哀。而在尼采之后提出的存在主义似乎多了一些玩世不恭的意味:这个世界是荒谬且没有逻辑的,而你我每个人也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的才来的,但是来都来了,起码做些什么再走——不过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东西可比什么超人哲学好实践多了。
《骆驼祥子》的选段在我上中学的那个时候还是语文书上的课文,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我建议各位有时间的话都去读一读这书的完整版,只要一两个小时就读得完了。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只有一个:祥子是怎么从任劳任怨的“骆驼”变成躺平摆烂、混吃等死的普通车夫的?或者说,这本小说里藏着“佛系”、“躺平”和“摆烂”的秘密:幻灭,然后虚无主义。一些被虚无主义所吞没的人不愿成为超人,甚至不愿意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在世界上踩几个脚印,而是躺在桥洞下盖着小被大声嘲笑往来的路人:他们陷入了现代犬儒主义,成了怀疑一切、嘲笑一切的玩世不恭之徒。但是,人大抵是不会甘愿躺在桥洞下的,因此现代犬儒主义还有一种粗俗且充满了蔑视的译法:狗智主义。不过这里暂时先放下“现代犬儒主义者到底和狗有什么区别”这种充满了人身攻击意味的讨论,因为共同的敌人看起来是虚无主义。
御宅族到底算不算是沉溺在虚无主义中的一种体现?从刻板印象来看,御宅族们似乎不事生产、专事消费,对着一些批量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垃圾发泄兽欲,简直是人间渣滓——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我隐约记得,御宅族的本意似乎是一些内向而拥有小众爱好的人,但是通常过度沉迷于自己的爱好而常常与世界脱节倒是真的。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刻板印象未必是全错的——比如与死宅们较了二十多年劲的庵野秀明创作 EVA 的动机。就我个人而言,对“死宅真恶心”一类的批评起码还有自知之明,但是对于一些孜孜不倦总想劝死宅“回归现实”的,我倒是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死宅如果不是生来就是死宅,那到底是怎么成为死宅的呢?难道不是因为现实有一些让死宅从中逃开的东西吗?回到马克思的“宗教-鸦片”比喻,如果不去解决现实的痛苦,却只是断了他们的鸦片,恐怕比整天抽大烟更致命吧。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罗曼·罗兰《米开朗基罗传》
罗曼·罗兰这句陈年鸡汤虽然早已泛滥,但毕竟不是人人都是英雄——“逃避虽可耻但有用”除了是一部电视剧以外,还是一句匈牙利谚语。如果现代犬儒主义或者御宅爱好或者什么其它的东西有助于从幻灭和虚无主义带来的自杀倾向中走出来,那它们在这种意义上就是有益的。如果你厌倦了这种玩世不恭的消极态度,存在主义可能是个好的开始。而如果当你开始觉得存在主义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时候,说明你已经鼓足了勇气,敢于直面世界的荒诞、无意义和人生的虚无了。
总而言之,暂时放下手机,然后从屏幕前离开、出门去走走吧。即使不像西西弗斯那样推动一块永远推不到山顶的石头,踢踢路边的石子也可以。哪怕是游戏里的糖糖也可以不碰魔法、不自残拿到 100 万粉丝金盾。
或者,这些话可能只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吧。
注释和参考文献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于东兴译,《齐泽克的笑话》,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第 90 页
↑3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第 75 页
↑4 https://zh.wikiquote.org/zh-hans/%E9%81%93%E6%A0%BC%E6%8B%89%E6%96%AF%C2%B7%E4%BA%9A%E5%BD%93%E6%96%AF
↑5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 4 页
分类动漫杂谈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