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梅洛-庞蒂笔记
source link: http://sht2019.cn/2022/01/18/351.mei-luo-pang-di-bi-ji/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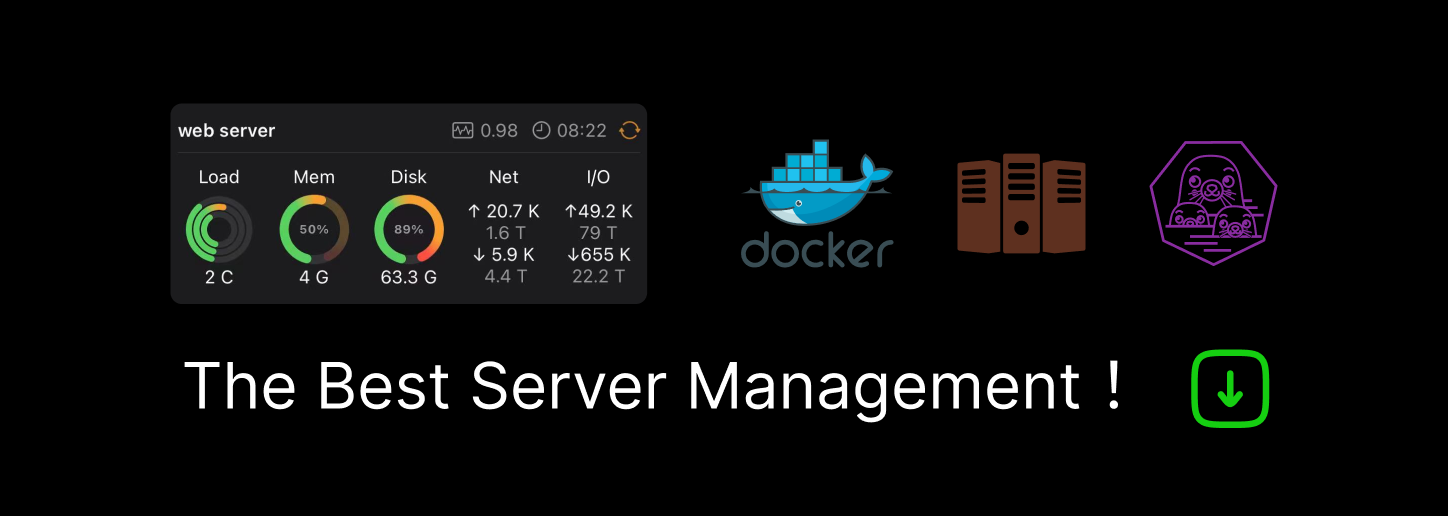
Maurice Merleau-Ponty - Wikipedia
《1961眼与心》
法文版前言
一小块蜡或粉笔,桌子,立方体,被知觉事物的这些过于简略的象征(emblfeme),
很经常地由哲学家们 提供出来,以便通过计算去消除被知觉事物。
他们全都迷恋于通过摆脱可感者去寻求心灵的拯救,他们会说,
这些事物之所以被选取,是为了证明我们所寓居的世界的悲惨。
相反,为了从视觉、从可见者那里提取这些哲学家向思想所要求的东西,
梅洛-庞蒂呼唤的整个地是一种景致,
一种已经通过眼睛吸引住心灵(esprit)的景致——在这里,近处之物弥漫在远处之物中,
而远处之物使近处之物产生震颤;在这里,万物的在场是在不在场(absence)
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在这里,存在与现象(apparence)相互交流。
“当我透过水的厚度看游泳池底的瓷砖时,我并不是撇开水和那些倒影看到了它,
正是透过水和倒影,正是通过它们,我才看到了它。
如果没有这些失真,这些光斑,如果我看到的是瓷砖的几何图形而没有看到其肉(chair),
那么我就不再把它看作为它之所是,不再在它所在的地方(即更加远离任何同一的地方)看到它。
水本身,水质的潜能,糖浆般的、闪烁的元素,我不能说它处于空间中;
它不在别处,但它并不因此就在游泳池中。它寓于游泳池,它在那里得以实现,
它并不被包含在那里。如果我抬眼看着反射光栅在那里起作用的柏树屏障,我不得不争辩说:
水也参观了柏树屏障,或至少把它的活动的、活的本质抛掷到了那里。”
当哲学把拷问推进到询问什么是思考,什么是世界、历史、政治或艺术,
以及什么是思想为其承担责任的全部经验时,纯粹思想只有通过接受纠缠着画家的谜,
通过在作品空间中把认识与创造联结起来,通过借助于语词让自己被看到,
才能够,才应该开辟自己的道路。画家在生活中或是强者或是弱者,但在他对世界的反复思考中,他是无可争议的主人,
他借助于他的双眼和双手的“技巧”而不是别的技巧努力去看、努力去画,
他发奋地从历史的荣辱都喧嚣其间的这个世界中,
提取一些既不会为人类的愤怒也不会为其希望增加任何东西、
而且没有人会为之窃窃私语的“图画”。那么,
画家拥有的或正在找寻的这种秘密的科学到底是什么呢?
凡高(Van Gogh)想凭着它走得“更远”的这一维度又是什么呢?
绘画的这一基础,或许还有全部文化的这一基础又是什么呢?人们看见的只能是自己注视着的东西。眼睛无任何活动的视觉会是什么?
如果眼睛的运动本身是反射的或盲目的,如果这一运动不敏感、不敏锐,
如果视觉不先行出现在运动中,那么眼睛的运动为何不会混淆诸事物呢?
我的任何移动,原则上都具象在我的景致的一角当中,都被划入到可见者之列。
我所看见的一切,原则上都属于我所及的范围,至少属于我的目光所及的范围,
都被记录在“我能” (je peux) 一边。可见者与“我 能”二者中的每一个都是完整的。
可见的世界与我的运动投射世界乃是同一存在的一些完整的部分。
神秘之处就在于:我的身体同时是能看的和可见的。
身体注视一切事物,它也能够注视它自己,
并因此在它所看到的东西当中认出它的能看能力的“另一面”。
它能够看到自己在看,能够摸到自己在摸,它是对于它自身而言的可见者和可感者。
这是一种自我,但不是像思维那样的透明般的自我(对于无论什么东西,
思维只是通过同化它,构造它,把它转变成思维,才能够思考它),
而是从看者到它之所看,从触者到它之触,从感觉者到被感觉者的相混、
自恋、内在意义上的自我—— 因此是一个被容纳到万物之中的,
有一个正面和一个背面、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的自我……。
这一原初的悖谬现象不停地产生出其他的悖谬现象。
我的身体是可见的和可动的,它属于众事物之列,它是它们中的一个,
它被纳入到世界的质地(tissu)之中,它 的内聚力是一个事物的内聚力。
但是,既然它在看,它在自己运动,它就让事物环绕在它的周围,
它们成了它本身的一个附件或者一种延伸,它们镶嵌在它的肉中,
它们构成为它的完满规定的一部分,而世界是由相同于身体的材料构成的。
这些颠倒,这些背反,以多样的方式表明:
视觉被纳入到事物的环境中或者说它是在事物的环境中形成的—— 在这里,
一个可见者开始去看,变成为一个自为的、看所有事物意义上的可见者;
在这里,感觉者与被感觉者的不可分割持续着,就如同晶体中的母液那样。
这种内在性并不先于人体的物质排列,更不会产生自这种排列。
假如我们眼睛以我们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会落入我们目光的方式构成,
或者,假如某种让我们手自由地抚摸事物的灵巧装置阻止我们触摸我们身体——或者说得简单些,
假如像某些动物那样,我们拥有的是无法让视觉场交会的长在两侧的眼睛,
那么这个不能自我反映、不能自我感觉的身体,这个几乎等于金刚石的身体,
就完全不会是肉,也不会是人的身体,也因此就不会有人性(humanite)。
然而,人性不是由于我们的发音、由于我 们的眼睛定位(更不是由于镜子的存在——
唯有它们能使我们整个的身体向我们呈现为可见的)而产生出来的结果。
人之为人必不可少的这些偶然因素以及其他相似的偶然因素,并不以简单求和的方式表明:
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身体的灵化并不是由于它的诸部分一个挨一个地配接,
另外,也不是由于有一个来自别处的精神降临到了自动木偶身上:
这仍然假定身体本身没有内在,没有“自我”。当一种交织在看与可见之间、
在触摸和被触摸之间、在一只眼睛和另一只眼睛之间、在手与手之间形成时,
当感觉者一可感者的火花擦亮时,当这一不会停止燃烧的火着起来,
直至身体的如此偶然瓦解了任何偶然都不足以瓦解的东西时,人的身体就出现在那里了……
由于万物和我的身体是由相同的材料做成的,身体的视觉就必定以某种方式在万物中形成,
或者事物的公开可见性就必定在身体中产生一种秘密的可见性。塞尚说:“自然就在内部。”
愿量、光线、颜色、深度,它们都当着我们的面在那儿,它们不可能不在那儿,
因为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引起了共鸣,因为我们的身体欢迎它们。
万物在我这里引起的其在场的这一内部等价物,这一肉体方式,
它们为什么不能够有机会引起某种仍然可见的、
任何别人的目光都将在那里找到支撑其审视世界的理由的轮廓呢?
于是,出现了一种派生力量的可见者,它是原初力量的可见者的肉体本质或图像。
这并不是一件弱化的复制品,一种假象, 一个另外的事物。画在拉斯科(Lascaux)
洞壁上的动物,并不像石灰层的裂缝或隆起那样呆在那里,但它们更不会在别处。
受到它们灵巧地利用的洞壁整体的支撑,这里稍商有前,那儿略微靠后,
它们向洞穴四周辐射,但从来没有挣断缚住它们的难以觉察到的缆绳。
我很难说出我所注视的图画在何处。因为我并不是像人们注视某个事物那样去注视它:
骗没有在它所在之处固定它,我的目光在它上面游移不定,就如同处在存在的各种光环中一样,
与其说我看见了它,不如说我依据它,或借助于它来看。
形象(image)一词已经声名狼藉,因为人们曾经轻率地相信:
一幅素描(dessin)就是一种移印(d&alque)、一个复制品、一个派生物,
而心理形象就是我们的私有杂物中的一幅这种类型的素描。
然而,就算形象事实上绝不是这样的,素描与画面也并不因此比形象更属于自在。
它们是外部的内部和内部的外部,正是感觉的双重性使这两种情形得以可能,
而没有它们,人们将永远无法理解准在场和准可见性——
两者构成为关于想象物(imaginaire)的全部问题。
图画、 喜剧演员的摹仿并不是我从真实世界借用的、
以便通过它们指向某些不在场的庸常之物的辅助物。
想象物非常接近又非常远离实际之物:非常接近,因为它是实际之物的生命在我身体里的图表,
是实际之物第一次展露给那些注视的肉质(pulpe)或它的肉体内面(envers charnel),
而在这个意义上,正像贾珂梅迪(Giacometti)着力指出的
那样:“在一切绘画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相似,也就是说,那对我而言乃是相似的东西:
那让我稍许揭示了外部世界的东西。”非常远离,因为图画只有依据身体才是一种相似物;
因为它没有向心灵提供一个去重新思考事物的各种构成关系的机会,
而是向目光提供了内部视觉的各种印迹(以便目光能够贴合它们),
向视觉提供了从内部覆盖视觉的东西,提供了实在的想象结构。
因此,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内部目光,有一只观看图画、甚至观看心理形象的第三只眼睛,
就像人们所说的有一只透过外部信息在我们身上引发的喧嚣来捕捉这些信息的第三只耳朵吗?
当全部事情就在于懂得我们的肉眼远非光线、颜色和线条的感受器时,这又有何用呢?
作为世界的计算器,眼睛拥有针对可见者的天赋,就像人们所说的,
有灵感的人拥有语言的天赋一样。当然啦,这种馈赠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够获得,
而且这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一个画家也不能够在孤独中开始拥有其视觉。
问题不在这里:不管是早熟的还是迟来的,是自发形成的还是在博物馆里培育出来的,
画家的视觉无论如何都只能在看中习得,都只能从它自身中习得。
眼睛看见了世界,看见了世界要成为绘画所缺乏的东西,
看见了绘画要成为它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在调色板上看见了绘画所期待的颜色;
一旦绘画得以完成,它就看见了回应所有这些缺乏的图画,而且它看见了其他画家的绘画,
看见了对于其他缺乏的其他回应。人们不可能对可见者进行限定性的清点,
就像不能够对某一语言的各种可能运用、或者仅仅对它的词汇表和表达法进行这种清点一样。
作为能够自己运动的工具,作为能够设想出自身目标的手段,眼睛是这样的东西,
它被来自世界的某一特定的影响所感动,并通过手的各种形迹把这种影响恢复成可见者。
在它得以诞生的某种文明中,在围绕它的某些信念、某些动机、某些思想和某些仪式中,
甚至在它看起来求助于别的东西的时候,自拉斯科直至如今,不管是纯粹的还是不纯粹的,
是具象的(figurative)还是非具象的,绘画从来都只是在颂扬可见性之谜而非其他之谜。
我们前面之所说属于一种老调重弹:画家的世界是一个可见的世界,
是可见的世界而非别的什么,是一个近乎不可思议的世界。
这是因为,尽管它只不过是局部的,但却依然完整无缺。绘画唤醒并极力提供了一种狂热,
这种狂热就是视觉本身,因为看就是保持距离,
因为绘画把这种怪异的拥有延伸到存在的所有方面;
为了了进入到绘画中,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让自己成为可见的。
当青年贝朗松(Berenson)说意大利绘画是对触觉价值的诉求时,他错得过于离谱了:
绘画不会诉求任何东西,尤其不会诉求触觉。绘画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几乎是相反的事情:它把可见的实存(existence)赋予给世俗眼光认为不可见的东西,
它让我们勿需“肌肉感觉”(sens muscu- laim)就能够拥有世界的浩瀚。
这一毫不知足的视觉,越过“视觉与料"(donnee visuelle)向着存在的某一织体
(texture) 敞开,那些不引人注目的感官信息只不过是它的标点或顿挫,
眼睛寓居于其中,就像人寓居于自己家中一样。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狭义的、寻常意义的可见者中:
画家,不论他是谁,只要他在作画?,都在实践一种神奇的视觉理论。
画家确实必成高意,要么万物进入到他那里,要么按照马勒伯朗士 ( Malebranche)
的嘲讽性的二难推理, 精神通过眼睛走出来,以便穿梭在万物之中,
因为它不停地根据它们调整它的超凡视力(voyance)。
(要是画家不 照模特儿画,也丝毫不会产生任何改变:无论如何,他在画画,
因为他已经看过,因为世界至少有一次把可见者的密码刻在了他身上。)
画家确实必须承认,就像一位哲学家说过的,视觉是宇宙的镜子或浓缩(concentration),
或者像另一位哲学家说过的,个别世界通过视觉向共同世界开放,最终说来,
同一事物在那边处于世界的中心,在这边处于视觉的中心,这同一事物——或者,
要是我们坚持的话,某一个想似事物,但根据的是效果的相似——乃是存在在他视觉中的近似、
发生和变形。在那里让自己被画家看到的正是山峰本身,画家通过注视拷问的正是它。
确切说来,何者为画家之所求?他之所求乃是揭示那些手段——那些可见的手段而非别的手段:
借助于它们,山在我们的眼里变成为山。光线、明亮、阴影、映像、颜色,
画家所求的这些客体并非全都是一些真实的存在:就像那些幽灵一样,
它们只有视觉上的实存。它们甚至只处在常人视觉的阈限之上,它们不能够被普遍地看到。
画家的注视向这些客体询问它们如何被捕捉到,以便让某种东西突然出现,
以便构成世界的这一法宝, 以便让我们看见可见者。 在《夜巡图》中,
当它投在卫队长身上的影子同时从侧面向我们呈现出它时,那只指向我们的手确确实实就在那里。
卫队长的空间性就维持在不能够同时可能却又属于同一整体的两个视点的交叉处。
阴影以及其他类似物的这种作用,凡是长着眼睛的人,总在某一天曾经看见过。
正是这种阴影的作用让他们看到了一些东西和一隅空间。但它影响他们却不用触及他们,
它为了显示事物而掩饰自己。为了看见事物,我们没有必要看见阴影。
常人眼中的可见者忘记了它的各种前提,它依赖于一种有待重新创造的、
将摆脱囚禁在它身上的那些幽灵的完整可见性。
就像有人说过的,现代画家已经摆脱了许多别的幽灵,
他们确实给我们的观看手段的正常音阶增添了一些听不到的音符。
然而,无论如何,绘画的拷问指向万物在我们身体中的秘密而躁动的发生。
安德烈-马尔尚 (Andrg Marchand)继克勒 (Klee)之后说道:“
在一片森林中,我有好多次都觉得不是我在注视着森林。
有些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注视着我,在对我说话……而我,
我在那里倾听着……我认为,画家应该被宇宙所穿透,而不能指望穿透宇宙……
我期待着从内部被淹没、被掩埋。我或许是为了涌现出来才画画的。”
当母体内的一个仅仅潜在的可见者让自己变得既能够为我们也能够为他自己所见时,
我们就说一个人在这一时刻诞生了。画家的视觉乃是一种持续的诞生。
至于镜子,它是具有普遍魔力的工具,它把事物变成景象,把景象变成事物,把自我变成他人,
把他人变成自我。画家们往往面对镜子出神,因为,
借助这一“机械技巧”以及借助透视(perspective)技巧,
他们认识到的是看者与可见者的变形,这种变形是对我们的肉的界定,
是对他们的天职(vocation)的界定。这也就是为什么画家们往往都喜欢——
他们现在仍然喜欢,我们只要看看马蒂斯(Matisse)的素描就知道了——画正在作画的自己,
在他们看到的东西上面补充事物从他们那里看到的东西,
似乎是为了表明存在着一种整体的或绝对的视觉,
在这个视觉之外,没有什么会持存,而这一视觉在这些东西本身上面合拢自身。问题在于知道“视觉是如何自己形成的”,但却处于这一必然的范围内:
在需要的情况下发明某些可以矫正它的“人工器官”。
人们更多地思考的是从外面进入到我们眼中并引起视觉的光,而不是我们所看见的光;
不仅如此,按照某种可以解释视觉的已知属性且能够由此推导出其他属性的方式,
人们在这上面还局限于两三种有助于设想视觉的比较。
如此把握事物,最好是把光线设想成一种通过接触的作用,
就像事物对盲人手杖的作用一样。笛卡尔说,盲人们“用手来看”。
笛卡尔的视觉模式乃是触觉(toucher)。
这个模式使我们立刻摆脱了有距离的作用,
摆脱了造成全部视觉困难(及其全部功效)的那个无所不在者。
为什么现在要去思考那些映像(reflet)、那些镜子呢?
这些非实在的复制品是事物的变种,如同球的弹回一样,它们乃是一些真实的效果。
如果说映像与事物本身相像,这是因为它差不多和事物一样作用于眼睛。
它骗过了眼睛,它引起了一种无对象的知觉,但它并没有影响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
在世界中,存在着事物本身,而在事物之外同时还存在着这种别的东西,
它乃是反射光,它与事物有某种有规律的对应,因此,
它们是通过因果性外在地联结起来的两个个体。事物和其镜像的相似,
对于它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外在命名,它隶属于思想。
可疑的相似关系在事物当中却是一种清楚的投影(projection)关系。
一个笛卡尔主义者是不会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他看见的是一个假人(mannequin),
一个“外部”。他有一切理由认为,其他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看他,
这个假人,对于他自己和对于其他人一样不是一个血肉之躯 (chair)。
他的镜中“形象”是事物的机械运动的一种效果 ,如果他在那里认出了自己,
如果他感觉到它与自己“相似”,那么正是他的思想编织了这种联系,
镜像绝不属于他。
如果不是通过相似,那么它是如何表象客体的呢?
它“刺激我们的思想”去“构想”,就像符号和言语构想“
不在任何方式上与它们所意指的东西相似的东西”一样。
版画(gravure)提供给我们一些充分的指示 ,
一些毫不含糊的“方式”来形成一种关于事物的观念,
这种观念不是来自于肖像,而是以肖像为“契机 ”(occasion)产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意向类别( espfeces intentionnelles)的魔力,
【已故著名法国哲学研究专家庞景仁先生译为“有意外貌”,并解释说,
“我们直接知觉到的只是物体外貌,这种外貌是物体通过媒介而传播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学说就叫做'有意外貌'。”这一解释来源是笛卡尔在回答别人驳难时说的一段话:
“我相信我们的感官所接触的东西除了被感官感觉或知觉的物体体积最外层的表面以外,
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接触只能在表面上接触,接触对于感官来说是非常必然的;
我认为,如果没有它,我们的任何一个感官都不能被触动,
而有这种看法的人不止我一个 ,亚里士多德本人以及在我之前的很多别的其学家都是如此。
因为,比如说,面包和酒,如果它们的表面不是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通过空气或者别的物体的办法,
像我认为的那样,或者像许多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
通过'有意外貌'的办法而被感官所触动的话,它们就不会被知觉。”】
效果相似的古老观念通过镜子和画面而为我们所接受,
如果画面的全部潜能就是推荐给我们阅读的一个文本的潜能,而绝没有把看者和可见者混杂起来的话,
这种魔力或观念就丧失了最后的论据。
我们不需要去理解关于事物的绘画在身体中如何会汀事物为心灵感受到,
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这幅赢与事物的相似也需要被看到,
因为我们需要“在我们大脑中的,可以用来瞧见这种相似性的其他眼睛”,
而且因为,当我们沉迷于这些在事物与我们之间游移不定的幻影时,
视觉难题整个地没有被触动。
光线在我们眼里以及由此在我们大脑里勾勒的东西与铜版画一样不相似于可见世界。
从事物到眼睛,再从眼睛到视觉,与从事物到盲人之手,
再从他的手到他的思想一样,并没有传递任何东西。视觉不是事物自身在其视觉中的变形,
不是事物双重隶属于大世界和一个私人小世界。
正是某一思想精确地识别出了身体中的那些给定的符号。
相似是知觉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动力。更何况,心理形象,
那让不在场者面向我们在场的超凡视力,绝不是一个朝向存在之心脏的钻头:
它仍然是一种依赖于某些身体标示的思想。这些标示这一次不那么充分,
思想让它们说出的要多于它们所意指的。类比的梦幻世界什么也没有留下……。
在这些著名的分析当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它们让我们感觉到,任何绘画理论都是一种形而上学。
笛卡尔并没有很多地谈到绘画,人们可能会觉得,
以他有关铜版画的两页之所言为依据,是不妥当的。
然而,如果说他只不过是顺便谈到了绘画,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绘画对他来说不是有助于确定我们通达存在的一种中心活动,
它是由理智的支配和明见性(Evidence)符合规则地规定的思想的一种方式或一个变种。
在他就绘画而说出的少量言语中,正是这种取舍被表达了出来,
而对绘画的一种更专心研究就会勾勒一种不同的哲学。同样意味深长的是,
应该谈到“画面”时,他把素描作为典型。我们将看到,
整个绘画呈现在它的每一种表达方式中:有一个轮廓,一根线条包含了它的全部大胆独创。
在铜版画中,
笛卡尔喜欢的是保留了诸客体之形式的或至少向我们提供了它们的足够标记的那一些。
这些铜版画通过客体的外表或客体的外壳向我们展示该客体。
如果笛卡尔曾经研究过面向事物的这一另外的、且更深入的开放(这一开放是各种第二性质,
尤其是颜色提供给我们的,因为在这些第二性质和事物的各种可变属性之间不存在着有规律的、
投射的关系,而且因为,它们的信息由于我们而获得理解)的话,
那他就已经面对着普遍性问题和无概念地向事物开放的问题了,
那他就不得不去研究颜色的含糊的低语如何能够向我们表呈事物、森林、风暴,
最后还有世界,或许他还不得不把透视作为一个特例整合到更广泛的存在论能力中去。
但对于笛卡尔来说,不言而喻,颜色乃是装饰,乃是上色,
绘画的全部能力取决于素描的能力,
而素描的能力又取决于在素描与自在空间之间存在着的有规律的关系
(就像透视投影教给我们的那种关系)。帕斯卡尔(Pascal)论绘画之肤浅的名言——
绘画让我们依恋于一些形象,而其原形(original)却没有打动我们——
乃是一句笛卡尔式的名言。对于笛卡尔来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只能够画一些现存的事物,
它们的实存就是成为广延,素描通过使广延的表象得以可能,从而使绘画得以可能。
绘画因此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技巧,它向我们的眼睛呈现一种投影,
一种类似于在普通知觉中事物在我们的眼睛里铭刻下的或将要铭刻的投影,
它使我们在真实客体不在场时,就如同在生活中看真实的客体一样去看,
它尤其让我们从并没有真实客体存在于其中的那个空间去看。
画面是一种平面的东西,它巧妙地把我们面对着“以不同方式画下来”
的事物时看到的东西给予我们,
因为画面根据高度(hauteur)和宽度 (largeur)
而把它缺少的维度的充分的区别性标记提供给我们。
深度(profondeur)是派生自其他两个维度的一个第三维度。
我们在这第三维度上停留一会儿,这是值得一做的。它首先有某种悖谬的东西:
我看一些彼此遮掩的物体,我于是并没有看见它们,因为它们一个在另一个的后面。
我看这第三维度,而它并不是可见的,因为,它把我们的身体包括在事物之中,
而我们与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神秘是一种虚假的神秘,
我并没有真正看到它,或者,假如我看到了它,它乃是另外一种宽度。
在把我的眼睛与视平线联结起来的那条线上,第一景致始终遮掩着其他景致,
如果从侧面我以为我看见了按等级排列的那些客体,是因为它们并没有完全彼此掩盖;
因此,根据以另外方式计算的一种宽度,我看到了它们一个外在于另一个。
我们始终没有达至深度,或者完全超出于它之外。事物永远不旱一个在另一个后面。
事物的侵越性与潜在性并没有进A 到它们的定义中,表达的不过是我与它们当中的一个,
即我的身体的不可思议的相互关联。事物肯定地拥有的一切归属于我形成的思想,
而不是事物的属性。我懂得,在这同一时刻,一个置身于别处的别人——
最好说无处不在的上帝—— 能够穿透它们的藏身处,看到它们被展示出来。
我称之为深度的东西其实什么都不是,或者是我参与到一个没有限制的存在中去,
首先是一个超越了全部视点的空间存在中去。事物彼此侵越,因为它们一个外在于另一个。
其证明是,通过注视一个画面,我能够看见其深度-所有的人都会同意,
画面没有深度,它为我组织了一种幻相的幻相……这种具有两个维度、
让我看到了它的另一个维度的存在,是一个有缺口的存在,
正如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扇窗户……然而,
最终说来,窗户只能向着一些部分外在于另一些部分的东西,
向着只能从另一侧面被看到的高度和宽度,向着存在的绝对实证性开放。
笛卡尔的空间相对于一种服从于经验且不敢建构的思想来说是真实的。
必须首先理想化空间,把这个在其类型上完美的存在者设想成清楚的、
易于操作的和同质的,思想没有视点地俯视它,
而且思想可以把它整个地移转到三条呈直角相关的轴线上,
为的是人们有朝一日能够找到建构的限度,能够明白空间并非像一个动物有四只或两只爪子那样,
不多不少刚好具有三个维度;这些维度是借助于各种各样的度量从某一维度、
某一多形的存在(它使全部维度有了保证,但并没有被任何一个完全地表达出来)中提取出来的。
笛卡尔拯救空间是有道理的。但他的错误在于把空间升格为摆脱了一切视点、
一切潜在、一切深度的,没有任何真正厚度的一种完全肯定的存在。
他从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技巧中获得启示也是有道理的:
这些技巧鼓励绘画自由地产生对于深度的体验,更一般地说对于存在的表达。
除非这些技巧企图宣告绘画的探索和历史结束了,企图确立一种精确可靠的绘画,
否则它们就不会有什么错误。
画家们本身都根据经验知道,任何一种透视技巧都不是一种精确的解决方案,
不存在任何方面都尊重现存世界的、值得成为绘画的基本法则的针对现存世界的投影,
线性透视绝不是终点,它相反地为绘画开启了许多条路子:
通过意大利画派开启了表现物体的路子,通过北方画派则开启了高空投影、
圆形投影以及斜投影等等路子。这样一来 ,平面投影法并不像笛卡尔相信
的那样总是能够刺激我们的思想去寻找事物的真实形式:
经过一定程度的变形之后,它反过来求助于我们的视点至于那些事物,
它们逃逸到了任何思想都无法穿越它们的远处。
空间中的某种东西逃避了我们的各种俯瞰的尝试。
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任何一种既有的表达方式能够解决绘画的问题,
能够把绘画转变为技巧,因为没有哪种象征形式会永远作为刺激物起作用:
象征形式之所以能够运作和发挥作用,正是由于与作品的整个背景相一致,
而绝非通过视错觉的手段。风格的要素永远摆脱不了某某个人的要素(Wermoment)。
绘画语言本身不是“由自然确立的”:它有待于创造与再创造。
视觉是一种受制于条件的思想,它“借机”从那种进达身体的东西中产生出来,
它被“刺激”去借助于身体而思考。它既不选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
也不选择要么思考这要么思考那。
它应该在其核心中承载着不可能通过外部入侵突然向它而来的这一重负,这一依存。
身体的这样一些事件是“由自然确立的”,为的是允许我们去看这看那。
视觉的思想依据思想并没有由它自己提供的某个程序和法则起作用,
它并没有掌握它自己的前提条件,它并不是完全在场、完全现实的思想,
在其核心中有一种被动性的神秘。情形因此是这样的:
我们就视觉之所说和所想的一切把视觉变成了一种思想。
比如说,当我们想要弄明白我们是如何看见那些物体的状况时,没有别的方法,
我们只能假设心灵能够(因为它知道它的身体诸部分在何处)
“把它的注意力转移”到处在肢体延伸部分中的全部空间点去。
但是,这仍然只是事件的一个“模式”。因为,思想将之延伸到事物中去的其身体的这一空间,
所有的密由之而出的这个最初的呼,思想是如何知道它的呢?
盲体空间并不如同那些事场一样是随便一种样式,广延的一个样本,
它乃是被思想称之为“它的”的身体之处所,是思想寓居的一个处所。
思想给予生机的身体对于它来说并不是诸客体中的一个客体,
而且思想并不以暗含前提的名义从身体那里引出全部其余的空间。
思想不是依据自身,而是依据身体进行思考。
如果说,为了眼睛能够达到如此调节度和会聚度,
心灵意识到了如此距离的话,那么从第一种关系中引出第二种关系的想法,
就仿佛是一种铭刻在我们内心工场中的远古想法:
“当我们手握某种东西时,这样的情形通常无须我们进行思考就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总是借助于手去适应该物体(corps)的大小和形状,去感受该物体,
我们无须为此去思考手的动作。”身体对心灵而言是其诞生的空间,
是所有其他现存空间的基质。视觉于是分身为二:有我对其进行思考的视觉,
我只能认为它是思想、精神审视、判断、征兆读解,而不是别的什么;
还有一种实际发生的视觉,作为一种名誉性的或被构成的思想,
它被挤压在它的某一身体之中,人们只在运用它时才会了解它,而且,
它在空间与思想之间引入了由心灵和身体复合而成的自主秩序。当我透过水的厚度看游泳池底的瓷砖时,我并不是撇开水和那些倒影看到了它,
正是透过水和倒影,正是通过它们,我才看到了它。如果没有这些失真,这些光斑,
如果我看到的是瓷砖的几何图形而没有看到其肉,那么我就不再把它看作为它之所是,
不再在它所在的地方(即更加远离任何同一的地方)看到它。水本身,水质的潜能,
糖浆般的、闪烁的元素,我不能说它处于空间中;它不在别处,
但它并不因此就在游泳池中。它寓于游泳池,它在那里得以实现,它并不被包含在那里。
如果我抬眼看着反射光栅在那里起作用的柏树屏障,我不得不争辩说:
水也参观了柏树屏障,或至少把它的活动的、活的本质抛掷到了那里。
画家以深度、空间、颜色名义寻找的正是可见者的这种内在灵化
(animation interne), 这种辐射。
当人们就此进行思考时,一个惊人的事实是:通常一个好的画家也画出好的素描或做出好的雕塑。
它们在表达手段与动作方面都没有可比之处,
这就证明存在着一种等价系统 ,一种关于线条 、光线、颜色、凹凸、主体的逻各斯,
一种关于普遍存在的无概念的表达。现代绘画的努力主要不在于在线条和颜色之间,
或者甚至在事物的具象表现和记号的创造之间进行选择,而在于增加等价系统,
在于中断它们对于事物外壳的依附—— 这可能要求人们创造新的材料或者新的表达手段,
但它们有些时候是通过反复考察和反复倾注,从那些现存的材料和表达手段中形成的。
例如,存在着一种关于线条乃是自在物体的实际属性和特性的庸常看法。
线条乃是苹果的轮廓或者翻耕过的田地与牧场之间的边界,它们被视为呈现在世界中,
是铅笔或毛笔只需一笔带过的一些虚线。
在者对于我们所见者和让我们所见者的这种先行,
我们所见者和让我们所见者对于在者的这种先行,乃是视觉本身。《1969世界的散文》
纯粹语言的幻象
我们在地球上说话已经很久了,而我们说过的四分之三的话都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了。
“一朵玫瑰”,“天在下雨”,“时光美妙”,“人是要死的”,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表达的纯粹情形。
在我们看来,当它没有歧义地指示事件、事物状态、观念或关系时,表达就处于其顶点,
因为,它在这些情形下没有留下任何可求的东西,它不再包含任何它没有揭示的、
使我们滑向它指称的对象的东西。而在对话,叙述,语词游戏,知心话,许诺,
祈祷,雄辩,文学中,总而言之,在这类具有第二力量的语言中,
我们只是为了打动某人才谈论事物或观念,语词在这里回应的是语词;
这类语言引起的是它自身,它在自然之上把自己构造成一个嘈杂而狂热的王国;
我们把它看作是那些陈述某种东西的标准形式的简单变种。
表达不外乎是以一个宣布、展现、简化某一知觉或某一观念的约定俗成的信号(signal)
来代替这一知觉或这一观念。当然,并非只存在着惯用语,
而且一种语言能够指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但是,如果新的成分不是从那些旧的、
已经被表达的成分中构造出来的,如果它不能够由正在使用中的语言
的词汇表和句法关系获得完整的界定,语言如何能够实现这种功能?
语言使用一定数量的基本的、与关键含义任意地连接在一起的符号。
它能够从这些关键含义出发重新组织任何新含义,从而能够用同一种语言说出它们。
最后,表达能够表达,是因为它把我们全部的经验重新引回到了我们在学习语言时
就已经掌握了的这个符号和这个含义之间最初一致的系统中;
语言之所以是绝对清楚明白的,是因为没有哪种思想会在语词中残存,
也没有任何语词会在关于某种东西的纯粹思想中残存。我们完全秘密地尊崇这一语言理想,
总而言之,语言通过把我们引向事物而使我们从它本身那里解放出来。
语言对于我们而言乃是这一令人惊异的装置(appareil fabuleus):
它允许用有限数量的符号 表达不确定数量的思想或事物——
这些符号被选用来准确地重新组织我们打算说的一切新东西,
被选用来向我们通报事物最初命名的证据。
既然这一装置的运作成功了,既然人们在说,人们在写,那么我们可以认为:
语言就像上帝的知性(Fentendement de Dieu)一样——
包含了全部可能含义的胚芽;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注定要被语言说出;
出现在人的经验中的任何含义在其自身内就包含着其用语,就像在皮亚杰(Piaget)的儿童们眼里,
太阳在其中心就包含着其名称。
我们的语言实际上从事物那里重新发现了一种扮演这些事物的言语。
这些信念并不仅仅归属于常识,
它们主宰着精确科学(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并没有主宰语言学)。
人们总是重复地说科学是一种正确地构成的语言。这也就是说语言是科学的开始,
而算法(algorithme)是语言的成熟形式。于是,算法把精心而圆满地获得界定的含义
赋予给选定的那些符号(signe)。它确定了一定数量的 透明关系,
并为表述这些关系而构造符号(symbole)—— 这些符号本身并不表示任何东西,
它们从来都只表示我们习惯上让它们表示的那些东西。算法就这样摆脱了引起错误的意义转移,
它原则上确信,能够在每一时刻都通过诉诸于那些最初的界定来完整地为它的陈述作辩护。
在涉及用同一算法去表达某些关系,而该算法不是为了它们而构成的、
或者表达如人们所说的那些“另一种形式”的问题时,或许就有必要引入新的界定和新的符号。
但是,如果算法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它打算成为一种严格的语言并在每一时刻都控制它的运算,
那就完全不需要引入任何暗含的东西。各种新旧关系最终必须一起构成为一个单一的家族,
我们看到它们从可能关系的某个单一系统中派生出来。
这样一来,永远不会出现我们打算说的超出于我们实际所说的,
或者我们实际所说的超出我们打算说的这样的情形。
符号停留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被完整地解释和证明的某种思想的单纯简化。
表达唯一的却是决定性的效力因此就是用我们真正为之负责的那些意指行为
来代替我们的每一思想对所有别的思想的混乱暗示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准确范围),
就是为了我们而恢复我们的思想之生命。而算法的表达价值停留在派生含义与原始含义、
原始含义与本身没有含义的符号的毫无歧义的关系中,
思想在这种关系中找到的只能是它置于其中的东西。
如果在我们结结巴巴说话中存在着语词取决于事物 本身这样一个语言的黄金岁月,
那么交流就没有任何神秘。我在我自己之外指示一个已经在说话的世界,
就像我用手指指示一个已经处于他人视域中的某个对象一样。
有人说面部表情的表达本身是有歧义的:脸红可以表示愉快、害羞、发怒、
狂欢造成的发热或红斑,这取决于指示它的情境。
同样,语言的手势表达对于注意它的那个人的精神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性,
它只是沉默地向他指示他已经知道其名的那些事物,因为这个名字就是它们的名字。
但是,让我们把关于事物的语言的神话放在一边,或者毋宁在其升华的形式中,
在普遍语言的形式中理解它—— 它预先包含了它必须表达的一切,
因为它的语词和句法反映了那些根本的可能性以及它们的关联。结论是一样的。
言语本身没有任何效力,没有任何能力掩蔽在言语之中。它是一种代表纯粹含义的纯粹符号。
说话者将自己的思想编成密码,他用一种发声的或可见的排列——
这不外乎是空气中的声音或者写在纸上的墨迹一取代他的思想。
思想是自知和自足的,它借助于一种并不携带思想、
只是把它毫无歧义地指示给别的思想的信息来宣告自己。别的思想能够阅读这一信息,
因为它能够借助于习惯、人们的约定或者神意的机制把同一含义与相同的那些符号联系在一起。
不论如何,我们在别人的话中寻找到的从来都不过是我们自己置于其中的东西,
交流是一种表面现象,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真正新的东西。
如果我们自己不拥有交流向我们展现的那些符号的含义,那些符号就不会向我们说出任何东西。
那么交流如何能够把我们引到我们自己的思考能力之外?
的确,当我观看像Fab-riee这样的夜间信号,
或者注视霓虹灯广告牌上缓慢的和快速的字母在静止的灯泡上移动时,
我在那里仿佛看到了消息的诞生。
某种东西在闪烁,它获得了生机,而人的思想隐匿在远处。但这最终说来不过是一种幻象。
如果我没有亲临那里感受其节奏并辨认出移动着的字母,
在那里有着的就只是一亮一灭的灯光的无意义闪烁—— 如同星星的闪烁,因为经过的电流要求它这样。
电报告诉给我的关于死亡和灾难的消息本身,也绝对不是一种消息,
我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我知道死亡和灾难是可能的。
当然,人们关于语言的经验并不是这样,他们狂热地喜欢与著名作家闲谈,
他们拜访他就如同瞻仰圣•皮埃尔(Saint Pierre)的雕像一样,他们因此暗中相信交流的秘密功效。
他们完全知道:消息只是消息,只要他们没有得知他们所爱的某人的死亡,
任何消息都无助于他们经常想到死亡。但是,一旦他们思考语言而不是体验之,
他们就不明白人们如何能够为语言保留这些能力。总之,我们明白向我们所说的东西,
因为我们事先就知道人们向我说出的那些词的意义。最终而言,我只能理解我已经知道的东西,
我只向自己提出那些我能够解决的问题。考虑一下封闭在他们自己的含义中的两个思考者的情形:
一些信息在他们之间循环着,但它们不表达任何东西,
它们只是使他们中的每一个注意到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的契机;
最后,当其中一个说而另一个听时,他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地、非正面遭遇地彼此再现。
如此一种关于语言的普通理论,正像波朗所说的,将会导致这一结果:
“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最终发生的一切仿佛是语言没有存在过。”科学与表达的经验
我的铅笔是近处的物品,而那些远处的东西在远处,在它和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尺度;
或者,就算我成功地把它与景致中的某一物品做了比较,
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同时把它与别的物品进行比较。
在那边的男人既不是1厘米也不是1.75米高,他是一个在远处的人,
其高度在那里是停留在他身上的意义,
而不是一种可见的特征,因为我对我的眼睛借以向我宣告他的那些所谓的迹象一无所知。
由此一部巨著,一出大戏、一首诗词作为一个整块出现在我的记忆中。
通过重新体验阅读或表象,我可以完好地唤醒特定时刻,特定语词,特定环境,和行动的特定转折。
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使记忆得以兑现 这种记忆是独特的,
它并不需要细枝末节以便处于其明证中,它就如同被看到的事物一样独特、一样取之不尽。
使我震动的、我一度由此真正意识到我在向某人说话的这一谈话,我完全知道它,
我明天可以把它讲述给那些对它感兴趣的人听。
但是,如果这一谈话真的像一本书那样使我感动,那么我就不需要将彼此相区别的记忆集中起来,
我依然将它如同一件物品那样握在手中,我记忆中的目光包围着它,
这足以使我把自己重新放回到事件的发生中,以便让一切一对话者的姿势(geste),
他的微笑,他的犹豫不决,他的言语—— 重新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地方。
当某个人(作者或朋友)懂得表达自己时,符号马上被忘记了,唯有意义存留下来,
而语言的完美就在于它能够不被觉察到。
但是,如果这本书只不过说了些我知道的东西,它就不会使我这般感兴趣。
借助于我带来的一切;它把我引向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之外。
借助于作者和我由于说同样的语言而约定的这些符号,它使我合理地相信:
我和作者处在那些既有的、可自由处置的含义的公共平面上。
它处在我的世界之中,然后,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那些符号的通常含义,
它们就像旋风一样把我卷向我将要通达的别的意义。在阅读斯汤达之前,
我已经知道什么是无赖,当他把收税的罗西描写成一个无赖时,我明白他想说的是什么。
但当收税的罗西开始处世时,不再是他成为了 一个无赖,恰恰是无赖成了收税的罗西。
我通过所有的人共同利用的这些语词进入斯汤达的伦理学,
但这些语词在他的手中经历了一种秘密的扭曲。随着交叉印证的增多,
随着更多的箭头指向我从前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果没有斯汤达我或许永远不会到达的这一思想领地
(他在其间使用这些语词的时机总是急切地揭示他赋予这些语词的新意义),
我也就越来越接近于他,直至最后根据他写下这些语词的意图本身来阅读这些语词。
如果不从某个人的面部表情和他的个人风格中捕捉到某种东西,我们就不会模仿这个人的声音。
于是,作者的声音以把他的思想引导给我而终结。
最初使我求助于所有人的世界的某些普通词汇和某些已经熟知的插曲(比如决斗或嫉妒)
突然充当起来自斯汤达世界的密使的角色,并且最终虽然说不是将我置于他的经验存在中,
至少也是置于这一想象的自我中(他在五十年中一直使这一自我伴随着自己,
与此同时在作品中实现了这一自我)。唯有这样,读者或者作者才可以借波朗的话说:
“至少在这一刹那间,我已经成为了你。”我创造了斯汤达,我在阅读他时成了斯汤达,
但这是因为他首先已经知道如何把我安置在他那里。读者的忠诚不过是想象中的,
因为他从这本书所是的可怕机器中、从这一创造各种含义的装置中获得力量。
读者与书的关系类似于相爱的两个人。先是两个人中的一个居于支配地位,
因为他更傲慢或更活跃;然而这种情形很快有了变化,另外一个,
更沉默、更有智慧的那一个开始控制。在表达的环节,关系被颠倒过来,书支配着读者。
说到底,心理学分析的是说话的人,它用语言来强调对我们自己的表达毕竟是自然的。
但这并不证明语言的最初功能就在于此。假定我想与他人交流,
我首先必须使用一种向他和向我命名那些可见事物的语言。
在心理学家的分析中,这一最初功能被预设为是给定的。
如果我们认为语言不再是人类关系的手段,而是认为它表达了各种事物;
如果认为它不再处在活的使用之中,而是像语言学家认为的那样,处在其全部的历史中,
并且是一种在我们面前展现的实在,那么心理学家对这一实在的分析,就像作家的思考一样,
很可能在我们看来是肤浅的。科学正是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它的诸多悖论中的一个。
正是它把我们更为可靠地重新带回到了说话主体。
客观的历史是(对于索绪尔来说任何历史都是)这样一种分析,它把语言,
更一般地说把制度与社会分解为无数的偶然事件。但历史不是我们通向语言的唯一方式。
因为那样的话,语言就会成为一座监狱,就会制约着人们对语言谈论些什么。
在人们就它谈论的那些东西中始终预设了它,它不再能够进行任何阐明。
由于被语言的目前状态所掩盖,语言科学本身不会获得语言的真理,而客观历史则会自我瓦解。
我们还需要去理解语言的这一共时意义。这要求颠倒我们的习惯。
正因为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被引向认为我们的表达形式与事物本身相符合,
而且我们在其它外来的说话方式中寻找被我们的说话方式很好地表达的东西的等价物。
我们似乎总是看到,在我们的语言中得以编码的经验的进程是随着对存在的表述而发生的,
因为正是透过语言我们学会了以存在为目标,愿意思考语言——
就是说愿意将语言还原为在思想面前的一个事物的状态,
我们始终冒着把我们的语言试图用以确定存在的那些进程当作对语言之存在的直观的危险。
但是,当语言科学(它其实不过是一种更多样化的、延伸到他人的说话方式中的言语经验)
告诉我们不仅别的说话方式不承认我们语言的规范,
而且这些规范是我们自己的说话能力的一种回顾的、非本质的表达时,这意味着什么?
不仅不存在能够发现所有语言的共同要素的语法分析,
而且并不是每一语言都必然包含着在其它语言中发现的各种表达样式的等价物一
在颇尔语(Peul)中是用语调来意指否定,古希腊语的双数(deul)在法语中被混同于复数,
俄语的体(aspect)在法语中没有对等物,在希伯来语中,
人们称作未来的形式在叙事中被用来标记过去,命名为过去的形式可以用于未来,
印欧语言没有被动式和不定式,现代希腊语或保加利亚语丧失了它们的不定式一
一旦我们仍然不能够把某一语言的表达进程还原为系统。
与活的使用相对照,词汇或语法的含义永远都只能是近似的。
在有些语言中不能够说“坐在太阳下”。因为它们用一些特别的语词来指称太阳光的辐射,
而把“太阳”一词留给那个星球本身。这就表明这个语词的语言价值只能够由它边上
的那些其它的语词的在场或不在场获得界定。既然我们对其它的那些语词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语言似乎从来都不说任何东西,它发明一系列的姿势,
这些姿势在语词之间表呈了一些如此明晰的差异,以至于语言行为在其重复自己、
印证自己和证实自己的范围内以不容置疑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义世界的状况和轮廓。
更进一步地说,对于这样一种倾向的分析来说,语词和形式本身立刻显现为第二位的实在,
是更为原初的区分活动的结果。音节、字母、措词和词尾是最初的区分的沉淀物,
这种区分这一次没有任何疑问地先于符号对含义的关系,
因为正是它使得符号的区分本身(区分成音素)得以可能。音素是言语的真正基础,
因为它们是通过对口头语的分析被找到的,并且在语法和词典中没有其正式的存在,
并不要求由它们自己意指任何我们可以指示的东西。但正是由于这个理由,
它们表达了能指的原初形式,它们让我们在既有的语言之下看到那种
使得含义和寻常符号同时得以可能的预先活动。就像语言本身一样,音素构成为一个系统,
也即音素与其说是有限数量的工具,不如说是一种调整音调的典型方式,
是把一种语言姿势从另一种语言姿势中区分开来的不会耗尽的能力,最后,随着差异更为精确、
更为系统,随着这些差异进入到它们自身得以更好地被连接的状况下,
并且进而暗示这整个过程服从一种内在秩序,
音素构成为一种向儿童示范成人所追求的东西的能力。
对于落山的太阳,我无法说出其光线恰恰是在什么时候由白向粉红转变的,
但它向我显现粉红光芒的时刻总会来临。我不能够说出在屏幕上显现出来的
这一形象在什么时候可以被称作是一张面孔,但它是一个显现在那儿的面孔的时刻总会来临。
如果,为了相信在我面前的这一张椅子,我期待着证实它完全满足了一张实在的椅子的全部标准,
那么我永远也完成不了;知觉先于依据某些标准的思想,并最终告诉我这些现象意味着的东西:椅子。
同样,尽管没有任何东西在普遍历史面前被说出来,还是有那么一天,
书籍和其它东西提供给我的符号会说出它来,到那个时候,我也已经理解了它。
如果我假定这些符号只不过唤起了我对在我身上负载着的纯粹含义的注意——
这一含义既重新掩饰又似乎在吸收人们为我提供的那些接近的表达,
那么我就放弃了理解什么是理解。因为语言的力量并不存在于由它安排的,
与我们的精神、与各种事物的单独面对之中,此外也不存在于那些指示存在要素本身
的最初语词所取得的优势之中,仿佛全部未来的知识和所有后来的言语都局限于组合这些要素。
语言的力量既不存在于语言将要通向的这一理智活动的未来之中,
也不存在于它由之而来的神秘的过去之中。在语言成功地安排了那些所谓的关键词,
使它们能够说出比它们曾经说出的更多的范围内,在它超越于它之作为过去的产物,
以至于让我们产生超越®f有的言语并走向事物本身的幻觉
(因为我们实际上超越了全部既有的语言)的范围内,语言的力量完全存在于它的现在之中。
在这一时刻,某种东西被一劳永逸地获得,被永久地确立,
而且可以以过去的表达活动发生过的方式被传递,
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领会到了理智世界某一片断或者达到了充分的思想,而是因为,
只要同一语盲处于使用中,或者只要科学家能够将它重新恢复到现在,
我们对这一语言的目前使用就是可以重复的。有限数目的符号、
措词和语词能够产生无限数量的使用这一奇迹,
或者语言意义把我们引向语言之外这一异与同的奇迹,这乃是说话的奇迹本身,
而谁要是打算用它的“开始”或者用它的“结束”来说明它就会看不到它的“进行”。
在言语的现在使用中当然存在着全部先前经验的重复,存在着对语言实现的呼唤,
存在着推定的永恒性,但这一切就如同被知觉事物为我们提供存在本身的经验一样:
在这一环节,被知觉事物在其当前明证中把某种开始显露的经验
和用于确证这一经验的没完没了的未来推断摄结在一起。
总之,我们已经发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符号、词素和言语并不意指任何东西,
它们只能够通过它们的结合才能够承载意义,交流最终由说出的语言之全体过渡到了听到的语言之全体。
说话就是在各个时刻详细地展开某种其原则已经设定的交流。有人或许会问如何会是这样。
因为最终说来,如果人们告诉我们的关于地球史的一切都是有根据的,
那么言语就应该有其开始,而且它与每个儿童一道重新开始。
儿童在语言方面从整体进展到部分(虽然为了开始,他本人只不过使用了其诸多可能性中的某一些),
这并不让人觉得惊奇,因为成年人的言语功能作为模式被提供给他。
他首先把成人言语领会成模糊的整体,通过一场往复运动,
出现在这一整体中的每一表达工具都引起了对全体的改动。
人类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这句话不可能依赖于已经确立起来的某一种语言。
有人会说它一定是由于它自己才有所意指。但这就忘记了,
交流的原则已经在此之前由一个人知觉到在世界中作为场景之一部分的其他人这一事实所给定。
这样,他人所做的一切和我所做的一切已经具有了同样的意义,
因为他的行动(就我是其观众而言)指向的是我要指向的同样的对象。
第一句话并不建立在没有交流之中,
因为它从已经是公共的那些行为中呈现出来并且扎根于已经不再是私人世界的一个感性世界中。
当然,第一句话提供给原始而沉默的交流的相当于或多于它从中获得的。
就像所有的制度一样,它将同类转变成人。它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对于我们这些处于其中并且知道它构成了什么样的哥白尼式颠倒的人来说,
可以合法地拒绝把制度的和语言的世界描述为相对于自然世界是第二位的、派生的那些观点,
并且合法地生活在对人的某种信仰之中。可是,就像所有的信仰一样,
这一信仰只是靠了某些外借之物才得以维持。如果它封闭在自身之内,
它就丧失了对它自己的意识,如果它没有认识到前人类的(p&humain)沉默,它就不再尊崇人。
第一句话在那些已经常见的行为之背景中获得其意义,
就像第一个制度在超越自发的历史的同时延续之一样。
既然人们无法在既有语言的运作中探究听者或读者借以从语言姿态走向其意义的这一运动,
第一句话的神秘就不会大于任何成功表达的神秘。
在两种情形下都存在着灵活的意义对私人场合的侵犯,这一意义对于自己要寓居其中的个体的无知毫不在意。
但是,只要被感觉到的东西被痍结成各种事物,
这一意义的空虚就是在个人生活的充实中准备好的,就像沸腾是在一股水里准备好的一样。
言语在某种意义上修正和克服了感性确定性,但在某种意义上又保留和延续之,
它永远不会完全穿透私人主体性的“永恒沉默”。还有,这种沉默在言语下面延续着,
它不停地掩盖言语,只要声音稍微有些远或者不清楚,或者那种语言与我们的语言很不相同,
我们就会在沉默面前惊愕地见证第一句话。
如果我们想在语言的原始的意指活动中理解语言,我们就应该假装从来没有说过话;
我们就应该对语言进行一种还原,没有这种还原,
语言就会通过把我们重新引导到它向我们意指的东西那里而在我们眼皮下自我掩饰起来;
我们就应该像聋子注视那些说话的人那样注视语言;就应该比较语言艺术与那些
不会求助于它的其它表达艺术,并且尝试着把语言看作是这些沉默的艺术之一。
语言的意义相对于绘画的意义可能会有某些优势,而且最终说来我们应该超越这种平行。
但是,唯有在尝试的努力中我们才会意识到是什么使得这种平行最终成为不可能的,
而且我们才会有机会发现语言的最根本的特性。
76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