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source link: https://plausistory.blog/2016/09/29/liu_nqh/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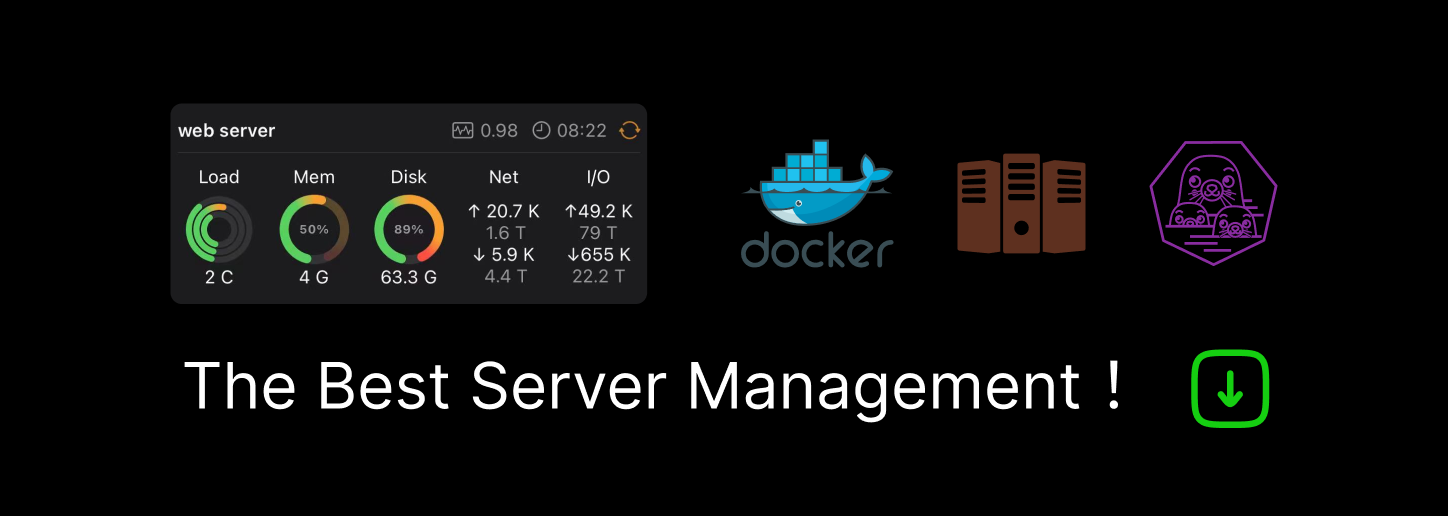
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曰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本文系201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会议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决策咨询及预研委托项目团队培育计划”项目成果(项目号15XNQ001〉,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致感谢。
所谓“新清史”,是指美国的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1]以重构清朝历史叙事体系为目的的一种学术思潮。[2]其目标在于解构汉化观下的历史叙事,反思清朝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定位。它以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EvelynS. Rawski)、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等人的著作为代表,着眼于满洲历史的起源,探讨清朝作为非汉政权的“满洲特性”,及其如何维系满人在文化和族群认同上的连续性等问题,[3]被认为标志着美国学界前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次重要转折,即“中国研究的族群转向”。[4]
然而,所谓“族群转向”只是这种学术思潮的一个表征。实质上,这种新叙事体系的建立,得益于欧美学界“内陆亚洲”(Inner Asia)历史研究理论的积累及其在清史研究中的应用,具体说是从内陆亚洲角度审视清朝历史,即以“内陆亚洲视野”,探寻“内亚因素”如何作用于清朝历’史的发展。因此,“内陆亚洲”才是形成“新清史”理论及所构建新叙事体系的基础性概念。
一、“新清史”的理论渊源与成长轨迹
在“新清史”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前,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史研究这一“族群转向”思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契丹辽的研究,认为征服王朝的统治者总是在其全部历史中保持着特权地位,而不会被汉化。但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80年代受到以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等为代表的汉化史观的批评而趋于弱化,后者则流行一时,成为显学。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满蒙等非汉文史料的获得和使用,并受傅礼初、法夸尔及后来的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等内亚史家的影响 和启发,以柯娇燕、罗友枝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更加关注女真一满人在清代历史上的主体地位, 并修正以芮玛丽为代表的汉化史观。[5]随着更多学者的加人及其著述的发表,这一思潮显然要比 魏特夫时代对契丹辽的研究更具持久性,且声势浩大。[6]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有学者开始 归纳这一思潮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在他们看来,清朝政权之中融合了众多的非汉因素,保持了 来自内陆亚洲的诸多文化特性,这不仅是清朝获得成功的关键,而且代表了内陆亚洲和东亚统一的顶峰阶段。[7]“内陆亚洲”研究视野的引人成为他们批评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汉化史观的重要理论武器。
在“新清史”学者看来,“内陆亚洲”研究视野将清朝历史的审视置于一种不同以往的空间和时间之中。在空间上,清朝在19世纪以前的统治重心被认为是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区,清朝在蒙、藏等边疆地区的成功,超出了传统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在以内陆亚洲为核心的国际空间中极具世界意义,对欧亚大陆宏观历史的发展影响重大。这种思潮提倡一种跳出“大汉族中心主义”的比较视野,来阐明清朝与中国其他王朝的不同、或与同时代其他亚洲、欧洲帝国的异同以及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关系。同时,从时间上看,清朝在内亚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表现出极强_灵活性,在内亚地区国际关系问题处理上,也早已打破以往的朝贡体系,呈现出与同时代欧洲殖民主义列强相似的特点。这些转变都构成清朝早期近代性与世界性的关键因素,对清朝的历史定位也由“帝制晚期”转向“早期近代”。[8]
随着欧立德等人著作的出版,盖博坚(R. Kent Guy)比较敏锐地注意到这种满人族群认同研究对重新思考清代历史的重要意义。他首先提出“满族研究四书”的说法,[9]这意味着美国学术界开始从这个以“内亚”为基础的思潮中提炼更加具体的“清朝的满洲特色”。然而,将这些研究仅仅定位于满族史,显然还不足以揭示内亚概念引入清史所带来的冲击,也不足以阐发出这些研究者胸中更为宏大的史学构想。利用内亚视野对汉化史观下的清史叙事进行新的全面修订,才是“新清史”学者要表达的一种史学志向,虽然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甚至受到质疑。
“新清史”的几位代表学者在这个概念的表述上也存在着差异。米华健所说的修订,不仅包括在研究方法上要借鉴人类学,重视满、蒙、苗等民族认同,并将清朝置于历史情境之下重新审视,更重要的是对“去中原中心观”的提倡,回到“以清为中心的清史”。他虽然将清朝重新定位为一个“内陆亚洲”的、同时也是一个“汉族帝国”,但包含了对“中原中心观”以及对将清朝视为一个中国王朝的质疑。他和濮德培、狄宇宙都倾于用“殖民主义”的观点审视清朝在内亚边疆地区的作为,以此看待清朝与中国王朝的不同。[10]欧立德也称清朝为“中国和内陆亚洲两个政治秩序的混合体”但实际上他的著作更强调清朝“内核”之中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即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族群主权”是保持满人有别于汉人的特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11]。因此,在他看来,“清帝国”在政治风格、政治模式、政治统治方面具有强烈的“满洲特色”,“清帝国”并非仅仅是一个标志时代顺序的时段名称,而是把清朝解释为一种非汉的、与明朝不同的王朝。在这层意义上,欧立德则试图将一些与清史研究关系密切的内亚历史研究者,如狄宇宙包括进“新清史”的范畴。[12]卫周安与米、欧二人视野相似,她也强调“新清史”的“去中原中心观”,认为“清帝国”自1636年形成之时,它的发展与构建便一直独立于中原影响之外,相对于“清帝国”在内亚的广阔疆域,中原只是帝国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但并非核心。因此,在“新清史”的范畴界定方面,卫周安力图把满人的独特性放大到“清帝国”国家构建的各个领域,这既包括满人作为“清帝国”的领导者如何实现其认同,也包括帝国在政治组织、皇室地位、民族政策、礼仪仪式、军事战争、皇帝出巡、妇女地位、艺术追求等所有能够反映与汉人政权不同的各个方面。所以,在卫周安关于“新清史”的范畴里,包括了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米华健、张勉治的著作,也包括曼素恩(Susan Mann)对18世纪妇女的研究、乔迅(Jonathan Hay)对艺术家傅山的研究等。[13]
由此可知,“新清史”学术思潮的兴起,有其复杂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看到“新清史”各著述中人类学研究、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等各种理论运用的痕迹,甚至可以发现它与日本学界研究满蒙历史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在这个层面新清史可以被视为“各类舶来学术观点的混合物”。[14]这也决定了即使在美国学术界,不同学者对“新清史”思潮的认知态度和表述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张力。其中,欧立德、罗友枝、米华健、濮德培仍在继续发表文章阐发相关观点。狄宇宙虽然没有关于清史的著作,但相关文章甚多。其他一些学者如张勉治等,不同程度在其著述中表达其受到新清史影响。但柯娇燕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属于新清史学派,自己的研究也不属于新清史,她对“新清史”的很多观点持批评态度。路康乐则在2000年的著作出版以后几乎没有更多的研究。这个学术群体呈现出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特点,呈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内部张力,
然而,笔者以为,不管这些学者是否认同“新清史”这个概念,或者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和争论,但是他们研究的基础共性不仅在于强调满蒙等内亚民族语言材料和考古成果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于是否以“内陆亚洲”为主要研究路径,把内陆亚洲理论运用到清朝历史问题的研究上,以此构建起清朝与内亚游牧政权的内在联系。概而言之,“新清史”思潮是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研究中的结果,此亦笔者所谓“内陆亚洲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新清史”这一思潮也被称为重构清史研究基础概念中的“内亚转向”(Inner Asian turn)和“欧亚转向”(Eurasian turn)[15]。欧美阿尔泰学自19世纪以来的学术积累和清代数量丰富的满、蒙、维、藏等非汉文文献,为这种转向提供可能,保证了“新清史”能够取得比以往辽金史研究更为引人瞩目的成就。
二、何为“内陆亚洲”
“内陆亚洲”本来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常与“中亚”一词交叉混用,在汉文中经常被翻译成“亚洲腹地”,其地理范围相对模糊。如司徒琳认为“内陆亚洲”是指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之间的森林、草原和沙漠等广阔区域,[16]但这也仅是一个大致范围。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内陆亚洲”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变得拥有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中。由于这个区域在地理范围上涵盖了中国西部、北部边疆地区,因此,“中国因素”,包括中国史料的运用、中国中原与内亚边疆的关系等,在“内陆亚洲”理论框架下显得非常活跃。回溯历史,“内陆亚洲”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初,欧洲地理学、汉学、阿尔泰学对它的界定和使用,二是20世纪上半期至80年代,美国和日本史学界对“内陆亚洲”理论的归纳,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清史”对“内陆亚洲”理论的运用和发挥。
(一)“内陆亚洲”的地理学意义
“内陆亚洲”一词最早被广泛使用于19世纪俄国的文献中,但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定型,源于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地理学家对“中亚”(Central Asia)地区的关注和研究,以及如何对亚洲的地理区域进行划分的思考,他们试图找到亚洲在地理上的中心区域。
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被认为是最早提出“中亚”概念的学者,他在1843年提出以北纬44.5°以北5°和以南5°之间的区域作为亚洲大陆的中央部分,目的是对亚洲中部地区进行定位,在这层意义上,“内陆亚洲”基本上等同于“中亚”、“中央亚细亚”。但这种标准受到俄国地理学家尼古拉•哈尼科夫(Nicolay Khanykoff)的质疑,后者于1862年提出以中亚缺乏注入外海的河流这一水文特征作为界定其地理范围的标准,其范围扩大到东部伊朗和阿富汗等地区,比洪堡的界定更加广泛。[17]此后,对“中亚”划分标准的讨论,推动了更多的地理学家按照从中央到边缘的视野对亚洲进行区域划分。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继续遵循以水文特征为主要标准,把亚洲地理划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亚洲的中心地带,即“中亚”,指南起西藏髙原,北迄阿尔泰山,西起帕米尔分水岭,东达中国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和大兴安岭,是一个封闭的、没有河流注人外海的内陆地区。在李希霍芬看来,长江、黄河的分水岭是由昆仑山向东的延伸;二是亚洲的边缘地区,是指所有河流流人大洋或里海或咸海的地区;三是过渡地带,位于前两者之间,指那些早先河流有出口而现已变成内陆河流地区或者是相反变化的地区。[18]此外,李希霍芬还提出一种著名的假说,即黄土髙原由风力搬运、沉积而成,并造就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不同,力图构建中亚草原、黄土髙原和东亚平原之间在地貌形成方面的整体性内在联系。[19]
19世纪晚期,俄国学者伊凡•莫希凯托夫(Ivan Mushketov)对李希霍芬关于亚洲区域的划分方法提修正,消除了李希霍芬所谓的“中间地带”,认为亚洲可以分为内陆和边缘两部分。对于前者,他沿用俄国文献中早已广泛使用的“内陆亚洲”名称,是指“亚洲大陆上没有河流注入外海,具有瀚海特色的一切内陆地区”。[20]相对而言,它比李希霍芬所说“中亚”的范围要广泛很多,李氏的“中亚”则指内陆亚洲的东部。
(二)”内陆亚洲”文化内涵的形成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随着越来越多欧美学者前往内陆亚洲地区旅行、探险,以及大量内亚文化资料的获得,“内陆亚洲”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得到更深入探究,“阿尔泰学”在欧洲汉学内部产生,并逐渐独树一帜。与地理学家相比,从伯希和(Paul Pelliot)开始,几代阿尔泰学家对“内陆亚洲”的范围界定都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
伯希和[20]曾使用“髙地亚洲”(La Haute Asie)—词来指代他极其广阔的研究范围,这几乎包括整个阿尔泰社会(蒙古和突厥)、西藏,有时又一直扩大到印度学和伊朗学。从地域上看,“高地亚洲”被概括为一个以帕米尔山区为中心,包括中国的新疆、西藏、蒙古在内的一个巨大的“弓形”地区。[22]伯希和以渊博的语言知识为基础,对“髙地亚洲”各族群语言关系进行旁征博引地辨识与考证,并由此研究他们的社会制度,揭示阿尔泰语系下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三类语族兴盛衰亡,及彼此间的渊源关系,包括各语族与中国历史的关系。
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提出“中央欧亚”的概念,视内陆亚洲为“中央欧亚”(the Central Eurasia)的东段部分,涵盖了北亚、蒙古髙原和中亚,并包括中国西藏和东北地区。但;由于东段地区历史文化丰富之程度、影响之深远实非西段能比,所以在塞诺看来“内陆亚洲”基本上等同于“中央欧亚”。[23]其范围从中国东北平原向西直到欧亚边界,从北部的西伯利亚向南到青藏高原、帕米尔、伊朗高原。内陆亚洲一方面具有髙山、草原、沙漠、森林、苔原带的地貌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些地貌又具有整体性。如山脉,帕米尔高原的山脉向东延伸与天山相接,再向东北方向与阿尔泰山相接,然后沿着北部西伯利亚的低矮山脉向东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平原。又如草原,从中国东北平原向西一直延伸到欧洲境内的匈牙利。[24]
狄宇宙认为“内陆亚洲”这一地带包括三个地理区域:中国东北平原,蒙古草原与森林和新疆的绿洲沙漠、草原,[24]其地理范围的界定是:东起中国东北平原,西至伏尔加河西部的草原地带,直至黑海,北部为西伯利亚的森林和针叶林地带,南部到中国农业社会边缘,西南为伊斯兰和东欧基督教世界的边缘。除了丝绸之路上的少数绿洲城市国家外,大部分地区都是草原、草场,北部边缘是森林地带,南部为沙漠半沙漠地带。[25]他基本延续了塞诺以非农业区的经济方式作为是否“内陆亚洲”的根据。
综上来看,与地理学家相比,内亚史专家没有遵循以封闭性水文作为界定“内陆亚洲”地理范围的原则,他们所谓“内陆亚洲”的地理范围显然要宽广很多。例如,中国东北地区从辽河流域到黑龙江飾域之间的范围并不具有内陆的地理特征,但依然被划入其中。但这两种界定都是跨国界和非政治化的。他们这样做的标准应该有两个:—是如塞诺所说“它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即不属于欧洲、中东、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那一部分”。[26]这种界定更加符合俄罗斯学者将亚洲分为边缘亚洲和内陆亚洲两部分的观点。二是更加关注每个地区生活的族群,其核心是不断迁徙的草原游牧民族,或者受游牧文化影响深刻、关系密切的族群活动地区。塞诺强调,在内陆亚洲不同的地貌范围中,由于森林、苔原、纱漠地带都不足以供养强大的政权,唯有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草原地带才是内陆亚洲的核心所在。[27]由于中国东北地区曾经是女真一满洲人的活动区域,并与蒙古髙原的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因此它也被内亚史专家列入研究范围。如此一来,文化意义上“内陆亚洲”的地理范围是由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族群文化的辐射范围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某些地理界限。
对内亚史专家来说,蛮族居住的“内陆亚洲”位于欧亚大陆的核心,而欧洲、伊朗、印度、中国等“外欧亚”地区成为文明外壳,整个世界以“内陆亚洲”为核心纽带联为一体。因此他们提出“内陆亚洲”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反思过去文明史观下的历史叙事,关注这个区域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以及这一区域被视为“野蛮人”的族群的历史主体性。他们从未独立于世界之外,而是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一直对世界各地文明史发展产生巨大的、关键性的影响,引起“定居文明社会”变革。这种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地区“野蛮人”自身的文化,如13世纪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成为一个世界帝国,虽然很快衰落,但在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留下的遗产,直到17世纪一直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清朝的建立[28]。另一方面,内陆亚洲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必经之地,东西方文明是通过内陆亚洲的“蛮族”传播的。然而,内陆亚洲及“野蛮人”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常被文明史观边缘化或忽视。正如巴菲尔德所说,定居文明,尤其是汉文化,虽然有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但很少用游牧民族自己的术语进行描述[29],即使有也多限于“干巴巴地列举入侵、胜利和战败”,其他则语焉不详。[30]实际上,这些“野蛮人”经常成为历史发展的主导者。在公元后的中国历史上,“蛮族”统治时期近二分之一,长达八百多年,“对野蛮人贪婪的忧虑自始至终浸透在中国的政策和文献里”。[31]
20世纪40年代,另一位对内陆亚洲研究有过重要贡献的学者是拉铁摩尔。与塞诺等内亚史家不同的是,他认为“内陆亚洲”这一术语既适用于中亚,也适用于比中亚范围更大的区域,主要包括内陆亚洲国家(地区),可以被定义为是那些没有海岸线的亚洲国家、地区。[32]实际上,他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中国西、北以长城为中心的边疆地带,包括新疆、蒙古、西藏和东北等地区,他更关注这些地区的“蛮族”政权在经济上对农耕区的依赖性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由此我们看到,“内陆亚洲”是一种极为宏观的视野,犹如将世界文明的空间进行了置换,拓展了世界历史的研究空间,改变了世界史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主义。[33]对于中国史研究来说,当以中国为视角时,这个地域变成了中国的边疆,而以“内陆亚洲”作为出发点时,“中国”成为边缘。
三、“新清史”对“内陆亚洲”理论的使用与发挥
有学者表示:“新清史”之“新”,并非因为有新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视角的转换,由过去以中原为中心变为以“内陆亚洲”为中心;强调历史主体的转变,由过去以汉族为主体转为以满、蒙等边疆少数民族为主体,发现这些“非汉”民族所建政权的“非汉”特性,发现这些民族在历史上的、过去被“汉化观”所掩盖的主体性,是“新清史”的主旨所在。[34]笔者以为,运用内亚理论对中国清代历史做出“新”的阐释,才是“新清史”之“新”所在,也是其获得重要学术成就的根基所在。但另一方面,从内陆亚洲研究的学术脉络来看,“新清史”对内陆亚洲理论的使用存在很多泛化、主观之处.
(一)满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陆亚洲特性”
“新清史”秉持“去汉化”的理念,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即“满洲因素”和族群认同在新清史学者们的历史叙事中扮演着浓厚而重要的角色•罗友枝探讨了以爱新觉罗皇室为核心的宫廷各方面体现出来的“满洲特色”,以此来证明清朝与汉人不同的特性。她甚至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依靠太监而统治”,[35]而清朝的各项核心政治制度、礼仪制度,以及太监奴仆等管理,都与汉人王朝不同。[36]对于这种满洲特性的来源,“新清史”研究者们大多认为与清政权根植于“内陆亚洲”有关,满洲文化深受内陆亚洲特别是蒙古文化的影响,与内亚地区游牧民蒙古人关系密切。[37]司徒琳将这种研究共性归纳为:满人正是充分吸收了蒙古提供的精要因素,建立了满蒙军事联合,形成了以直接税收为标志的、形态最高级的“内亚政权”,“代表了蒙古传统的精华”,保持了鲜明的“非汉”的“内陆亚洲”特点,并取得那里诸多民族的支持,然后以此为基础实现对中国的统治。[38]所谓内亚政权的“蒙古精华”归根结底是一种游牧文化。
这其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新清史”研究者们所说的“满洲特性”,实际上是对蒙古人的游牧文化特性移植的结果,这样的移植是否合理?第二,是不是所有满汉的不同,都可以被列入满洲特性?“满洲之道”所包含的骑射、纪律等品质,在塞诺那里被描述成为“内亚战士”的形象。从塞诺到傅礼初,他们所论证的“内陆亚洲文化”相当于以蒙古髙原为核心的游牧民族文化,但显然,上两代内亚史学者在阐述游牧民族的政治文化如何作用于其他民族时是非常谨慎的。
很明显,满人既不是游牧民族,也没有生活在蒙古草原,他们有着与游牧民族非常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满人虽然仿效、借鉴了很多蒙古人的因素,包括文字的创制、理藩院的建立等,但是满人不可能在一个广袤无垠的草原上进行游牧,也无法仅仅借助游牧开展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满人需要以定居为基础的狩猎、采集、农业作为经济支撑。对满人来说,获得稳定的经济支持才是第一位的,人主中原远比征服内亚更具吸引力。即使在战争方面,满人与蒙古人的态度也截然不同。18世纪50年代清军最终击败准噶尔部,平定内亚边疆,却没有像蒙古人那样继续无止境地深人“内陆亚洲”。乾隆皇帝以极具自我约束力的边境原则,拒绝了哈萨克、布鲁特内附的请求,表现出明确的“中国观”。[39]在对待西藏文化方面,满人表现的与蒙古人非常不同。出于政治需要,皇太极表现出对黄教的荨崇,鼓励蒙古人信仰喇嘛教。但他认为喇嘛教“甚属愚谬,嗣后俱宜禁止”,告诫满人对此保持警惕。[40]这种态度也表现在某些城市的布局上。皇太极扩建的盛京城,满汉宫殿位于城市的核心区,藏传佛教建筑位于城市外围,表明各种文化在大清王朝中的不同位置。[41]这种建筑风格后来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移植到承德的整体布局上。
由于内陆亚洲地区族群的复杂性,其文化也是变动不居的。清朝解决内亚边疆地区民族政治认同与归顺的方式是具体而多样化的,就像乾隆皇帝被视为多重象征:满蒙的大汗、藏传佛教的活佛、汉人的皇帝等等。但即使清朝皇帝治理边疆不同族群的文化政策再灵活,也仍然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在乾隆平定回部以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清朝并没有找到一个介人到南疆地区穆斯林文化的方法,也一直无法消除这个地区穆斯林对和卓家族的认同,其文化政策并不成功。[42]因此,清朝在边疆地区的稳定统治与其说是靠不同族群对“满洲特性”、“内陆亚洲特性”的认同,不如说是靠精心设计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强大的武力。
实际上,傅礼初把蒙古人和满人区分得很清楚,他所说的不易汉化、不易接受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是蒙古人,而不是满人。傅礼初曾明确表示,到19世纪,满人已经无可挽回地汉化了。米华健也曾指出:欧立德没有对19世纪满人族群认同的情况进行研究,且只关注了八旗满洲和八旗汉军,对八旗中的蒙古人缺少关注,对八旗中满人与蒙古人的关系、彼此是否有认同,缺少研究。[43]与满人相比,蒙古人才是真正的“内陆亚洲”民族。而且,即使是蒙古人,其“特性”也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成吉思汗以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各蒙古汗国逐渐与当地的文明涵化,导致有些蒙古人丧失其旧有的认同,消融于其他民族和国家之中。[44]无论满洲皇帝如何费尽心力地提倡和维护“满洲之道”,无论满人在心里面保留了多少认同,但一个不争的史实是各地满城的围墙无法成为满汉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当代学者的很多研究也证明了满汉不同族群之间文化交流的客观性:满人的衣食住行各种习俗在汉人中间流行,同时他们也接受了汉人的语言、习俗、文化。满汉之间的交流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双向互动[45]。所谓“满洲化”,实际上仅仅存在于康雍乾几代皇帝的主观意志和满人上层统治者之中。在晚清,象征满洲之道的满语、骑射等毕竟更加迅速地被遗忘、遗弃,而且,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反倒逆转了满汉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对比,进一步加大了满人在经济方面与汉人的差距。即使在政治上,满人也不得不依赖汉人精英来平定国内叛乱、维护内亚边疆的安全,以及应付西方的侵略,类似的情况在整个内亚都比较普遍,曾经叱咤风云的游牧政权,在西方人的进攻下,大多土崩瓦解。没有汉人精英的支持,清朝很难抵挡伊斯兰力量和俄罗斯人的威胁,以及蒙古人的反叛,有失去整个内陆亚洲边疆的可能。
(二)关于清朝在中国史和内亚史上的位置
“新清史”学者“去汉化”的目的是为了构建清朝与内亚边疆地区在文化上的联系,对此罗友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清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走向成功和强盛的关键是,其有能力对清帝国之内居住在“内陆亚洲”地区的非汉民族实行灵活性的、具体的文化政策,以获得他们对清朝的政治认同。[46]实际上,新清史学者构建文化联系的目的是要构建清朝与内亚政权,特别是与蒙古政权之间在政治上的延续关系,否定与中国传统王朝的连续性。
“新清史”学者们认为清朝是一个内亚政权,而非排在中国历代王朝序列之中的王朝。[47]这种观点的依据至少有三点:一是清朝在1636年就已经建立,8年以后才人关统一中国。[48]二是皇太极称帝的一个最主要契机是从成吉思汗后裔那里得到了传国玉玺,意味着清朝政权合法性的建立。三是入关之前,满人的文字、制度等大多借鉴蒙古人而来,满洲文化与内陆亚洲特别是蒙古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清朝被认为是“承袭蒙古帝国特质”的根植于“内陆亚洲”的政权,在这层意义上,狄宇宙认为可以将清朝在内亚地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努尔哈赤时期到1635年清朝建立之前,满人征服了内蒙古,取代成吉思汗的后裔获得蒙古的领导权。第二个阶段从1636年到1691年,以康熙时期的多伦会盟为标志,喀尔喀蒙古归顺清朝。第三阶段则从1691年到1750年,清朝击败在青海的蒙古势力,获得在青藏地区的统辖权。第四阶段,18世纪50年以后,以平准战争的胜利为标志清朝彻底击败厄鲁特蒙古。[49]
“新清史”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颇为接近。探讨内陆亚洲的满蒙地区相对于中国的独立性,是日本“清朝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如冈田英弘认为清朝是承袭蒙古帝国衣钵建立的一个新帝国,[50]而且其主要根据之一即1635年皇太极从林丹汗遗孀和儿子那里得到传国玉玺而称帝,标志着满洲政权接续了北元在内陆亚洲统治的合法性。[51]杉山清彦也据此提出,蒙古人对元朝的历史地位与汉人有着不同理解,汉人倾向于元_明一清的历史序列,而在蒙古人看来,北元继续保持了元朝的政治余绪,并未因为明朝的建立而中断,清朝承袭于北元,而非明朝。[52]
在一定程度上,“新清史”学者构建清朝与内亚游牧政权的联系,符合傅礼初关于历史现象中的“关联性”(interconnections)与延续性(continuities)的观点,也开拓了我们对清代历史的多维理解。所谓关联性是指不同域社会间发生的横向的交流现象,例如思想观念、制度层面的传播与贸易的联系等;延续性则指地域社会内部制度模式的贯时性、纵向的延续。[53]在“新清史”学者们看来,清朝不但与内亚蒙古政权之间存在着政治文化的延续性,而且与内亚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濮德培、狄宇宙等都做了很多类似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路径得益于傅礼初、法夸尔的启发。
相对于塞诺的早期内亚史研究来说,傅礼初以其卓越的内亚语言文化知识致力于后蒙古时代的整体内亚史比较研究。在傅礼初看来,“内陆亚洲”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内在因素,但在16—18世纪,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呈现出一种平行的整体史的发展规律。[54]他更注重对蒙古政治文化的提炼,并分析它如何作用于16—18世纪大清王朝、奥斯曼帝国等强国。另外一个对满洲政权的蒙古因素进行了启发性探讨的是与傅礼初同时代的法夸尔,他认为在历史上,除了满人,任何外族人从来没有成功管理过蒙古族,而满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满人的诸多文化、制度和观念如何承袭于蒙古人,这包括努尔哈赤大汗的称号、国家的概念、文字等,所以在1691年前.,满人对蒙古人进行管理的制度多起源于蒙古人自己的创造,1691年以后,当蒙古人全部商顺清朝后,汉人的制度开始产生直接的影响。[55]相对于以往内亚史家来说,此二人的研究进一步构建了内亚与清朝历史的关系,由此17世纪以后清政权如何受到蒙古因素影响变得由远及近地清晰起来,这极大地启发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崛起的“新清史”学者们。
然而,“新清史”学者们似乎有意忽视了清朝与明朝及其他中国王朝之间的延续性,也忽略了满人与同时代的汉人的关联性。虽然他们时常提到来自内亚的“每个王朝都同时吸收了东亚和中亚的因素”,[56]“在定居的农业世界和其外的草原游牧世界之间,设法创造出一个连续统一体”,[57]但新清史学者没有真正就清朝的“中原因素”进行论述,或构建出清政府内部东亚因素与内亚因素的平衡关系。由此,一个人口达到数亿的汉人族群全体在“新清史”的叙事之中几 乎缺失。这至少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本身,或者说,新清史学者在运用内陆亚洲理论反对和解构 “汉化史观”的时候,显得矫枉过正。
一些生活在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经历和见证了明清易代的连续性,他们留下来的实际记 录在证明“新清史”学者的主观臆断性方面非常具有说服力。这些传教士包括卫匡国、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白晋(Joachim Bouvet)等人,他们一方面感受到满人作为异族人侵、朝代更替过程中的残酷性,但也关注到满人在吸收汉文化方面的主动性。“不可否认,他(指卫匡国——笔者注)记述了满人的一些野蛮习俗,但他随即补充说,满人一人主中原,就放弃了这些习俗。他以充足的证据来说明,在征服之前,满族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58]另外一方面,他们对当时现实的描述,“给人这样的感觉:满人的统治一在北京确立,清朝便以一个传统的中国王朝的面貌出现”。安文思“简单地将清朝看作漫长的中国王朝序列中最近的一环”,白晋认为,“在康熙朝,儒家文化与满人尚武精神相互融合,达到理想的和谐状态”。汉人的因素对清朝的建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所以,唐纳德·F·拉赫(Donald F.Lach〉等在归纳这些传教士们的感受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满族人兴起于中原之外,欧洲人仍日益倾向于将他们刻画成一个新王朝实质上的创造者,他们对满族征服的解释,大都强调明清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包括讨论礼仪之争的文献在内,在对17世纪最后几十年关于这场征服的描述中,残暴、毁灭似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59]
因此,把清朝对内亚的征服看作与汉人和中原无关的事情,是有失偏颇的。狄宇宙对满人征服蒙古历史阶段的划分,虽然看上去比较合理,但历史的实际是,在狄宇宙所说的四个阶段中有三个阶段是清朝人主中原以后才得以实现的。而巴菲尔德注意到,清朝之所以能够对蒙古各部各个击破,可溯源到1571年明朝对蒙古的政策,即直接封赏每个小部落,这使得每个部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愿被成吉思汗后裔统一起来,各部落之间为了争夺这些利益矛盾重重。[60]现在看来,后金和清朝是这个政策更大的获益者。濮德培也指出,“新清史”学者们(指阿尔泰学派——笔者注)的研究过多地关注清朝的统治精英和边疆,却忽略社会经济结构与中心地区,也割裂了满洲精英与人口占主体的汉人的联系•他主张用一种“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的视角联结和看待清朝与明朝、内亚的关系。[61]
与13世纪蒙古人席卷亚欧大陆的征服战争不同,满人对内亚边疆的征服,需要建立在两个条件基础上.第一个条件是满人如何获得经济上的支持•战争的长期性、巨大耗费,决定了清朝在有了一个坚实的满汉联盟以及由此而来的充裕的财政支持后,才有能力进一步展开与准噶尔争夺内陆亚洲霸权的战争。在拉铁摩尔看来,内亚地区充满生机与活力,是中国历代王朝历史发展动力的“贮存地”,与内地即农耕民族居住区之间在经济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大中国”范围内的边疆地区,与中国内地具有高度的互相依存性。[62]就连“新清史”学者濮德培也明确表达出中原的支持对清朝西进的重要性。对清朝在康熙时期与准噶尔部的那场战争来说,后勤补给显得至关重要。深人漠北寻找准部主力决战的清军,在耗尽补给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遇到了噶尔丹的军队。再晚些天,补给断绝的清军将不战自溃。而为了准备这次战争,康熙皇帝从1690年开始,用了六年时间做准备,通过内蒙古的五路驿站,将后勤补给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63]雍正初期,清朝一直在秘密筹备在西北与准部的决战,这也是军机处成立的初衷。但雍正帝到底为筹备西北战事花了多少钱,耗费了多少物力、人力,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研究。乾隆时期清朝击败准噶尔部、回部的战争共花费了1000多万两银子。乾隆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表示,这种财政支出与雍正时期在西北地区的耗费相比节省多了。若不是已经入主中原,这种巨大的财政投人对满族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技术进步在中间也起着主要作用,如巴菲尔德说:“到18世纪中叶,随着技术与运输革命的到来,双方力量的军事均衡开始决定性地有利于周边定居文明,而游牧力量被统一进俄国与中国日益拓展的帝国之中。”[64]
第二个条件是满人能否在政治上纠正蒙古因素中的致命缺陷。如前所述,傅礼初指出,一个非汉政权能否持久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从维护部落贵族权势到强化官僚制度和君主集权制度的过程中,有效地克服游牧政权中固有的那种离心因素。在元代的宫廷之中,曾反复出现过流血政变,主要出自两派政治力量的角力,一派主张以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利益为准则,极力维护草原政治传统,一派则接受汉人的官僚制度,强化皇权。[65]相对而言,满人更成功地借助汉文化强化了皇帝的中央集权,成功克服了“血腥的竞争继承制”的缺陷。[66]因此清朝在其近300年的统治中,尽管也曾矛盾重重,甚至剑拔弩张,但他们保持了团结,宫廷内部未出现过严重的流血冲突。可见,满人在中国建立统治的过程、路径、方式及效果,都是与草原游牧政权非常不同的。学界的很多研究表明,在入主中原、平定全国的战争中,满人的政治领袖从多尔衮、顺治帝到康熙帝,在诸多关键时刻,经常表现出对满人本身实力不济的担忧,不得不依赖于汉人的支持,接受和利用汉人的文化、政治制度。[67]与汉人的联盟,有内地的支持,满人才能获得在内陆亚洲地区的成功,而不是把汉人当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对象。
(三)“新清史”将“内陆亚洲”演绎为一个政治概念
如上所述,“内陆亚洲”经历了—个从地理概念向文化概念的转变,犹如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地区的研究,从伯希和、塞诺到傅礼初等人—直在论证“内陆亚洲”似乎是一个“超越国界范围的地理和文化的统一体”。[68]但也正如“地中海世界”,虽然有经济、文化上的诸多共性,但它由很多族群政权构成,除了曾有过蒙古人极其短暂的统―,各个族群政权一直各自为政,互相征战,绝非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经济文化的差异与政治上的统属并没有必然联系。所以,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研究,到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研究,跨国界、跨行政区域的研究非常有助于我们对一个地区长时段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规律的捕捉,但并不是要否认国家或行政区域这种政治实体的存在。
伯希和认为,公元以后,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先后逐鹿中原,北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处于异族统治下,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第一次实现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并且把世界的各个部分密切联系到一起。[69]伯希和表示新疆(南疆)是操突厥语穆斯林生活的地方,但她在政治上属于中国。[70]
相对伯希和和塞诺而言,傅礼初更充分地把内亚理论用到对中国清代历史的审视上。首先,傅礼初的研究几乎颠覆了当时费正清主导的把中国的世界秩序纳入朝贡体系框架之中的企图。傅礼初以充分的内亚语言材料证明,明清时代的中国已经按照国家关系处理与内亚政权的关系。明太祖朱元璋曾企图将内亚政权如帖木儿帝国视为藩属、将其纳人朝贡框架下,但这一政治动机受到严重挑战。永乐时期帖木儿帝国为此与明朝几乎诉诸武力,朱棣有时不得不采取灵活的方式处理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视之为平等的政治伙伴。清朝虽然依赖强大的武力将天山南北地区成功纳人国家版图,但对版图以外的内亚政权如浩罕汗国等,清朝并没有拘泥于宗主一藩属,而是视之为国与国的关系,甚至不惜做出某些主权让步,以免喀什地区受到浩罕汗国的攻击。以后,随着俄国威胁的逼近,清朝又以建省的方式巩固了对这个地区的管理。[71]
在傅礼初那里,游牧政权的政治传统、文化和宗教,成为被北方民族政权广泛承袭、且对其历史发展有着关键性影响的因素,他非常强调位于“内陆亚洲”的蒙古、新疆、西藏地区对大清王朝的影响。傅礼初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适合游牧人信仰的宗教,所以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同时认为儒家伦理与汉化佛教与草原观念格格不人,因此反对蒙古人儒化、汉化的观点。但是,这些族群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到傅礼初对“中国”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些地区并不是与“中国”对立的,他毫不迟疑地用“清代中国”、“中华帝国”的概念覆盖这些地区,将这些地区视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认为它们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72]
在界定清朝所统辖的内陆亚洲地区与中国的关系时,傅礼初专门指出,“满洲”作为—个地理名词,是欧洲人的称呼,不是汉人也不是满人的称呼•满洲是中国行省制度的组成部分,从法律角度来看,它不是一个附属国。对于蒙古,傅礼初也指出,“蒙古是中国典型的边疆,因为蒙古的游牧民自古以来就几乎是对中国农业文明的不断的军事威胁。”清朝把生活在内蒙和外蒙地区的蒙古人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而且,傅礼初明确指出,在19世纪,满人的汉化已经不可避免,清末的奉天省早已主要成为汉人的地盘。
傅礼初还力图站在内亚的角度,以宏观视野构建中国的“现代性”,他认为19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欧洲人的到来和西方的影响,二是汉族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三是中华帝国边疆拓展和领土面积扩大一倍。18世纪中叶完成的疆域拓展,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中,一直在被慢慢地吸收人中国的版图,19世纪中叶以后的穆斯林叛乱和俄国人的到来,加速了这些边疆地区的现代转变。但傅礼初认为学者们主要专注于前两个因素的研究,很少关注领土面积扩大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的影响。
然而,“新清史”的研究者们演绎了“内陆亚洲”理论,把长城以南的地区称为“中国本土”(China Proper),是“新清史”学者们普遍采用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大清王朝是由内陆亚洲和内地两部分组成的。所谓“中国”是汉人的中国,长城即是边界,长城以外属于“内陆亚洲”,生活在这里的满、蒙等民族都有着强烈的“内陆亚洲特性”,他们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这些特点,即使他们人主中原,也没有被汉化,没有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由此认为,内亚地区非中国,清朝非“中国”,扩而言之,非汉民族建立的各个政权,是不是“中国”都成了问题.中国的内亚边疆地区被从中国“割裂”出去,“中国”成为内亚以外的他者。
由此来看,新清史”有关“清朝非中国”之观点的得出,关键点有二。—是以“民族认同取代国家认同”,二是把“内陆亚洲”作为他们演绎族群理论的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并上升到政治空间。“内陆亚洲”由一个地理概念和文化上近似的统一体,在不知不觉间被解释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并可以与“中国”这个国家概念、政治概念相抗衡。所以,“新清史”以内陆亚洲为基础构建其“去汉化”、“去中国化”的理论,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也违背了“区域研究”的本义•“中国”是一个政治概念,“内陆亚洲”政治实体化的结果是否认了历史上“中国”作为跨内亚、多民族政治实体的存在,否定了古代中国对边疆地区和非汉民族统治的合法性,将蒙、藏、疆,乃至东北满人居住发源地等内陆亚洲边疆移出“中国”范围,然后得出“清朝非中国”这种类似于“白马非马”的逻辑结果。
虽然“新清史”研究者一再声称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傅礼初等人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内陆亚洲”概念的“政治实体化”并非自伯希和至傅礼初等内亚学者的本义,反倒是更倾向于表达出20世纪以来日本学界将蒙元以降的中国肢解为“内地”和“内亚”两部分、努力使满蒙地区“去中国化”的意思•柯娇燕对此也曾提出过批评。她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日本学者为了论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领土的合法性,以及他们建立“满洲国”的正当性,曾经大肆宣扬阿尔泰主义语言假说,他们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警惕的。[73]
“新清史”在美国之滥觞由来已久,是内亚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史上的结果,代表了自费正清以来西方学界以“现代化”范式探讨清代历史之后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学术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开始从欧洲汉学中脱颖而出,标志着国际上对中国的研究重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其内容重点由以哲学、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汉学”转移到更为具体的中国历史,其研究目的由对“文明的解读”转移到对历史发展原因和趋势的探究。[74]实际上,与这种转移相伴的,是以塞诺为代表对中央欧亚和中国内陆亚洲边疆问题研究的重心也正在从欧洲向美国转移。
“新清史”对非汉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视和挖掘,可以给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观念很多启发。毕竟,中国历史有相当长的时间与内陆亚洲历史有着“无法分割不可分离的重叠”,受到内陆亚洲的影响,不断把内陆亚洲的因素吸收到中国历史中来,是中国历史自身的重要特点•从这个角度看,“新清史”内陆亚洲视野的引人会让我们的历史叙述更加丰富和立体化。[75]
然而,“新清史”将“内陆亚洲”地区非汉民族的文化特性混同于政治归属,将“内陆亚洲”从一个地理、文化概念异化为政治实体概念。这种“泛政治化”的做法不仅脱离了其原有的意义,也直接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合法性形成否定,这就显得非常主观了.
把中国想象成为一个单纯的汉民族国家,是“新清史”研究者们的一种假设,并非历史实际。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超越某种单一民族认同的国家,多民族走向统一是一种逐渐强化的发展趋势。中国边疆各个民族与汉族之间是一种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对中国历史的解释需要立足于中国历史本身的实际情境,需要西方学者真正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固有窠臼.
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指出的那样,“新清史”学者们虽极力表示对非汉语资料的重视,但对这些材料的使用方面仍出现了很多问题,真正能够以非汉文材料为主体支撑的研究还十分有限。[76]西方学者用内陆亚洲理论和资料阐释清代历史,还存在诸多问题。[77]随着在“新清史”思路下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年轻学者的登场,将“内陆亚洲”视野运用到清代中国历史研究上,还将出现更多发展和变化。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周群、吴四伍。责任编审:路育松)
[1]2004年,“新清史”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使用,是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欧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主编的论文集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一书出版,使用了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一词,也称 “New Qing History”。二是卫周 安(Joanna Waley-Cohen)以“New Qing History”命名的书评文章发表。对于“新清史”思潮的起源 时间,欧立德认为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米华健认为始自20世纪90年代。考虑到柯娇燕 (Pamela Kyle Crossley)等的一些文章最早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拟采取第一种说法。
[2]学术界有人称之为一个“学派”,如张勉治(Michael Chang)在他的著作中称,他对乾隆南巡的研究受 到了 “新清史”,即清史研究中的阿尔泰学派(Altaic School of Qing history)的影响。这里,他所说的 “学派”不仅包括柯娇燕、欧立徳、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还包括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以及前几代学者如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法夸尔(David M. Farquhar)、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黄培(Pei Huang)等。 (Michael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t 1751-1784, 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9)中国国内的学者如定宜庄教授也称之为“新 清史学派”。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仍存争议,如被视为新清史当然代表的柯娇燕也明确反对有所谓“新清史学派”的存在。笔者以为,正如柯文(Paul Cohen)所概括的“中国中心观”,“新清史”也是一种学术思潮。
[3] R. Kent Guy,“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1 (Feb. 2002), pp. 151-164.
[4] James A. Millward et al.,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4, p.4.
[5]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8.
[6] 柯娇燕在这一方面具有开拓性,并影响巨大,她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有关满洲起源、八旗制度 的文章,如 “Manzhouyuanliukao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6, no. 4, 1987, pp. 761-790,并于 1990 年出版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Qing Worl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之后,美国学术界与这一思潮有关的著作接连出版。
[7] Evenlyn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4 pp.829-850
[8]司徒琳:《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满学研 究》第5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司徒琳的观点来自于对1999年“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学术会议论文的总结.此次会议由司徒琳召集,在印第安纳大学召开,虽然还 没有“新清史”之名,但欧立德、米华健、濮德培(Perter Purdue)狄宇宙等满族史研究者和内亚史 研究者悉数与会,对清朝与内陆亚洲关系的关注是此次会议的一十重要议题。会后出版论文集: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Lynn Struve, ed.,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9] 盖博坚所说“满族研究的四书”即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Evelyn S. Rawski,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这种说法后来也被称为“新清史四书”,参见R. Kent Guy,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pp. 15-164.米华健等认为应该再加上柯娇燕的另外一部著作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Qing World,可见他们也认同“新清史四书”的说法(James A,Millward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但实际上,柯娇燕并不认同“新清史”这种说法,路康乐也没有明确的学术表态。
[10]James A. Millward,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 1759-186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7-18.
[11]Mark C. Elliott, The Md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 p.6.
[12] 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学术季刊》(台北)2006年第24卷第2期
[13]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 88 (winter 2004), pp. 193-206.
[14] 罗新、郑诗亮: <狄宇宙谈内亚史研究>•«东方早报> 2015年4月12日,第2版
[15] 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 Bost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5-7.
[16]参见司徒琳:《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满学研究》第5辑.
[17] A.H.丹尼、V. 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第366页
[18]斯文•赫定(Sven Hedin):《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第四纪研究》 2005年第4期。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黄土与中亚环境》,刘东生、张黄骏编译,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年,第 36—38 页
[19] A. H.丹尼、V. 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1卷,第367页。
[20]伯希和是一名卓越的汉学家,被誉为阿尔泰学的开创者之一。1906一1908年,受法国政府的支持和派 遣,他率领探险队在新疆、甘肃一带考察,因获得敦煌经卷而闻名一时。此后伯希和的研究重点转向 阿尔泰学,即研究汉族社会的边缘地区,是最早对内陆亚洲展开研究并获得重大成就坤学者之一。
[21] 德尼(Jean Deny):《法国阿尔泰学研究先驱伯希和》,《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3期。(耿昇译自巴黎 亚细亚学会1946年出版的《伯希和》)
[22]塞诺是伯希和的弟子,被认为是国际阿尔泰学界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内陆亚洲”的研究方面做了更多开创性工作。他于20世纪60年代由欧洲专赴美国,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创建了以 “内陆亚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参见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 研室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译者前言”;钟焓:《一位阿尔泰学家论内亚史: <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评述》,《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
[23]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Taipei: SMC Publishing, 1991, pp. 19-40.
[24]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1-20.
[25] Nicola Di Cosmo, Allen J. Frank and Peter B. Gold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
[26] 丹尼斯•塞诺:《什么是中亚》,《民族译丛》1986年第1期,喻融融摘译自《第十七届国际阿尔泰会议 论文集》,1976年.
[27]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 1-18.
[28]Nicola Di Cosmo, Allen J. Frank and Peter B. Gold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
[29] 丹尼斯•塞诺:《论中央欧亚》,《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页.
[30]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序言”
[31] 丹尼斯•塞诺:《北方野蛮人之贪婪》,《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31页.
[32]欧文•拉铁摩尔,《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内亚路径》,《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 170—177 页。原文 “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曾在 1947 年 4 月举行的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研究年会上宣读,并刊发于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57 ,pp.180-187.
[33] 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华工商联合会,2014年,第 6页.
[34] 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中国史学评论>(创刊 号)2014年1月。
[35]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p.162.
[36]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pp.7-8.罗友枝 这种看似非常“新鲜”的叙事,实际上贯穿了一种罗列的方法和非此即彼的逻辑,因此在美国国内也 受到批评.吴秀良(Silas Wu)在对罗著的书评中认为罗友枝的观点先人为主,其论述并不足以支撑其 观点.书评载于: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05, no. 3 (Jun. 2000),pp. 903-904.
[37]Evelyn S. Rawski, “The Qing Empir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 in James A. Millward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pp. 15-21.
[38] 参见司徒琳:《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满学研究》 第5辑.
[39] 郭成康: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 2005年第4期,第1—18页。
[40] 《清太宗实录》卷28,天聪十年三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56页.
[41] 李声能:《满族文化对盛京城规划建设的影响——兼论盛京城在满族和清代都城史上的地位》《满族研究》,2009年第3期。
[42] 欧立德: 《乾隆帝》,靑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2—143页。
[43] James Mill ward, Review Essay: Mark Elliott, The Manchu Way,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62, no.2(Dec. 2002), pp.468-79.
[44]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页.
[45] 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清史研究》 2000年第2期.
[46]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p.7.
[47] 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学术季刊》(台北> 2006年第24卷第2期
[48] Joanna Waley-Cohen, MThe New Qing History,M pp. 193-206.
[49] Nicola Di Cosmo, Allen J. Frank and Peter B. Gold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39.
[50] 岡田英弘:《世界史のなかの大清帝国》,岡田英弘主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年, 第59—73頁。
[51]冈田英弘:《满洲获得大元传国玺——清朝正统性的根据》,《蒙古学情报与资料》1991年第4期,第 56—59 页。
[52] 杉山清彦:《マンジュ国から大清帝国》,岡田英弘主編: 《清朝とは何か》,第74—91頁。
[53] Joseph F. Fletcher,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 1800,M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vol.9, 1985, pp.37-57.
[54] Joseph F. Fletcher,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 Mpp. 37-57.
[55] 戴维•法夸尔:《满族蒙古政策的起源》,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杜继东译,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198页,
[56] 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pp.829-850.
[57]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 88 (winter 2004), pp. 193-206.
[58] Donald F. Lach and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A century of Adv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1664.
[59]Donald F. Lach and Edwin J. Van Kley,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A century of Advance. pp. 1671-1672.
[60]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5页。
[61] Peter Pu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ofCentral Eurasia. Boston: Belknap Press, 2010, pp. 542-543.
[62] 拉铁摩尔:《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
[63] Peter Pu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ofCentral Eurasia. p. 159.
[64]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页,
[65]牟复礼、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66]“血腥的竞争继承制”是由傅礼初提出的一个概念,指蒙古人在汗位继承过程中充满激烈的竞争和杀 戮,造成巨大的离心倾向。这种政治文化对内陆亚洲地区的其他政权如奥斯曼帝国、清帝国都产生了 —定影响。参见钟焓:《傅礼初在西方内亚史研究中的位置及影响》,《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北 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1—250页。
[67] 魏斐德在对清朝开国历史的研究中一直试图证明以平定三藩之乱为标志,汉人的支持不但使清朝在军 事上获得成功,而且构建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参见氏著:《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4-392页)近年来,魏斐德的这一观点也受到挑战,姚念 慈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阐明康熙皇帝重满轻汉的内心情结,但不管康熙帝在对待汉人方面如何纠结, 平定三藩之乱还是不得不依赖汉人将领和军队的贡献。(参见姚念慈,《康乾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 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51—58页)
[68] 弗朗西斯•奥班: <约瑟夫•弗莱彻的蒙古史、满族史研究》,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0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58页.
[69]丹尼斯•塞诺《怀念伯希和》,《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402—415页。
[70]伯希和:《离地亚洲3年探险记》,《伯希和西域探险记》,耿昇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第8页。
[71]傅礼初:《中国与中亚1368—1884>,费正清编: <中国的世界秩序》,第199—215页。
[72]傅礼初:“清朝在亚洲腹地”,参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73] 侯德仁:《柯娇燕:我对“新清史”研究的保留意见》,《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9月1日,第A05版。
[74] 王晴佳:《中国有文明史吗?》,《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75]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中国国际出版集团,2014年,第90—91页。
[76] 钟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上)一是多语种史料考辩互证的实证学术还是意识形态化 的应时之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7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6-213页。
[77]柯娇燕曾写书评对米华健等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提出批评,认为该书没有对“内陆亚洲”、 “满洲帝国”等概念给出准确定义,所收文章非常草率,也没有实质性内容。(参见Pamela Kyle Crossley, “Review on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e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69, no. 1, 2006, pp. 169-171)
刊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144-159页。根据原文扫描件识别得来,如有文字差异,以原文为准。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