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西镇“发小”
source link: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6641a801030hmi.html
Go to the source link to view the article. You can view the picture content, updated content and better typesetting reading experience. If the link is broken, please click the button below to view the snapshot at that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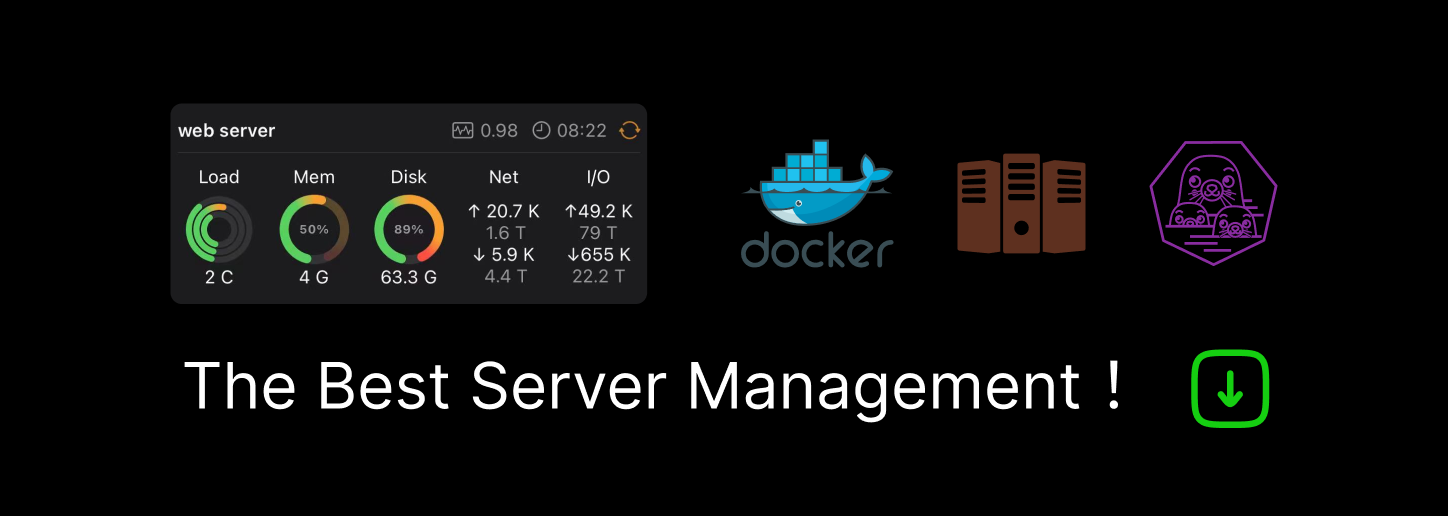
我的西镇“发小”
(2020-12-23 17:08:48)
2020年10月4日晚上,我与发小在青岛武胜关宾馆聚会,畅谈了三个多小时,依然意犹未尽。早在2012年6月,我和发小们聚会过一次,当时想写篇回忆文章,但是由于很忙,就放弃了,这次趁热写一写西镇,写一写我的发小。这些故事发生在青岛城市的西部,发生在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代。镶嵌在记忆里的童年,纯粹,热烈,质朴,散发着肆无忌惮的活力。故事共分为三个部分:一、里院里的九户人家;二、1960年代的故事;三、我的五个“发小”;四、我曾想成为诗人。
2012年发小聚会,可惜缺了华儿
2020年发小聚会,可惜缺了小会儿
一、里院里的九户人家
最近这些年,我介绍自己时多了一个称谓——“西镇小哥”,这个称呼标注着我在青岛西镇长大的背景,也寄托着我对青岛里院的牵挂。
嘉祥路路口
我出生在嘉祥路。嘉祥路是青岛的一条等高线马路。这条路上,除了德国人建的传染病医院(后来的台西医院)和国民党沈鸿烈市长建的第五贫民院(五院)以外,街区多是由一个个里院组成的。我住的里院叫铁工厂,门牌号为嘉祥路30号,对面里院是观海楼和西海楼。
我们里院共住着九户人家,院子中间原来有个空旷的天井。据研究青岛城市史的李明说,作为最具功能性的公共空间,里院的院内配备了厕所、自来水、下水道等设施,开敞的部分,最早则用来存放货物。可能在1958年大炼钢铁之时,我们院搬进来一家铁工厂,从此这里被称为“铁工厂”。
里院的外貌
青岛的里院一般以街道为边界,形成若干半封闭的院落,周边多是二至三层、四层的围合建筑。一个里院接着另一个里院,环环相扣,层峦叠嶂。一个或者几个门洞进来,里院的内部空间豁然敞开,类似柳暗花明,别有洞天。一个院子里的人,大家共同一个水龙头,吃饭的时候把饭桌摆在院子里,邻居们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吃饭,相互之间非常和睦。这种和睦关系,成了培养我的社交能力的最早起点。记得我经常到隔壁刘家吃饭,他们家做了好吃的都有我的份,楼上各家我也是随便去,上床下地,随意玩。我父母叫他们刘太太、刘先生、张太太、张先生等,大家彬彬有礼,和睦相处,很少发生过争论。中国的运动几乎在每个乡村都展开了,城市的运动是围绕单位展开的,青岛城市里的里院没有成为运动的单元,所以我们这个里院一直维持着中国式的邻里关系。
我们住的里院是个小二楼,一楼住户逐步被铁工厂吞食,一楼仅剩两户人家,我家和隔壁刘家。这篇文章关于邻家我用的是我父母的说法。我家除了父母,我还有两个姐姐。刘家的刘大爷是养殖厂的工头,身上有纹身,院里的小孩都怕他。后来听说他的英语很好,是美国兵把他从烟台带到青岛的。刘大娘是个贤妻良母,他们家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下面是两个女孩,一个叫环,一个叫华,环和华是我的发小。
2020年我和环儿、华儿合影
二楼住着七户人家:王大娘家、龙朱家、马本基家、沙家、苏老太家、张家和李家。王大娘是我们院儿的小组长,她家里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比我大的叫王世法,最小的女儿叫小三。在我刚刚懂事时,跟小三有很多交流,可惜她二十几岁就生病去世了。王大娘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在她眼里,我是一个老实孩子。她总是说她担心我太老实,长大了结婚后会让媳妇欺负。记得她曾几次说这件事,并表示很担心,我就笑而不答。
龙朱家有哥儿俩,比我大几岁的叫龙朱。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很愿意跟我聊天,给我讲了很多故事,还经常讲一些黄色段子。文革初期,街上一片抓人声,他给我讲外面的恐怖,把我吓得够呛。可惜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马本基在邮局工作,他已经搬出院子,但他的母亲还在院里住,我叫他母亲马大娘。据说马本基是青岛邮电局的一支笔,青岛邮电局的历史都出自他之手。马家从黄县来,我奶奶娘家也是黄县的马家疃,所以我们两家有点亲戚关系。马大娘带着两个孙女一起住,其中小孙女叫小会,是我的发小。
沙家父亲叫沙美顺,在中山路红星电影院对面的银行工作,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其中老大沙宏伟是我的发小。记得那个时代总有一些重大的游行活动,我们几个发小就会结伴去银行的楼顶平台上观看。
李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比我大。李家的儿子叫西亮,十分聪明,因为父亲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不服气,在厂里挨了很多整。我上初中的时候跟他有一些交往,记得我在心里嘀咕过他为什么叫西亮,是不是想让西方亮?他家小女儿的女婿是个西装裁缝。记得上中学时,一段时间我对服装剪裁十分着迷,就利用去李家的空隙时间,向他学习剪裁。西装剪裁和中式剪裁最大的不同是量体,量好基本数据后,剪裁过程严格按照数据关系剪裁。摸到窍门后,我经常给邻居裁剪衣服,有时候三分钟就可以裁一条裤子。
我的发小中有一个搬离了这个院,住进对面的里院,这就是顾家。他们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小儿子叫大里,比我大一岁,也是我的发小。和我其他发小不同,双方父母给我和大里认了干亲,我跟他母亲叫娘,他跟我母亲叫妈。至今大里提到我母亲,仍然叫妈。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院共有三人考上了大学,除了我,还有隔壁刘家的刘丛启,二楼王大娘家的王世法。当年能考上大学的人很少,这个院能出三个大学生,让周围邻居很是羡慕。凑巧的是,我们院文革之前也出过三个大学生。
2012年发小聚会大合影
后来我才意识到,铁工厂占据我们里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使得我们院人口少了,彼此较为和谐,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好的环境。相比来说,西镇的很多里院人很多,比较杂乱,青岛人称之为“大杂院”,导致人际关系渐趋复杂,争吵打架的事情经常发生。
二、1960年代的故事
我1956年出生,1963年上小学,1970年上中学,我的发小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中期。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突然文革开始,大家都不上学了,所以我和发小有更多的时间到处疯玩,每天都出去。留在记忆中比较深刻的印象,是抓人斗人的恐怖场面和欢声笑语唱歌跳舞的情景。那时候,有大批串联青年,就住在我们院隔壁的新康旅社。
我的发小里面,有两家在文革中被遣返回了农村。记得都是我们游玩回来时,突然看到一辆大卡车停在某家门口,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卡车上。一下子,我的发小就被眼前景象吓傻了。不由分说,红卫兵把小孩抓到大卡车上,拉走了。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看到这样的场景,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我们院共有两家被遣送到农村,文革后期他们都回到了城市,但是两家男人都在农村自杀了。王友琴写文革死难者名单时,我想把这两个人的情况说出来,但是他们家里人都不愿意。中国人对待痛苦经历往往采用回避和隐忍的态度,这既有宽宏大量的一面,也有不能吸取教训的一面。
文革最严重的几年,我的主要发小都到了农村。我们院里铁工厂的分裂愈演愈烈,每次运动来临,我们家隔壁这个屋就成了关人的临时牢房。记着先后关的有资本家、走资派、造反派头目。我们家后来搬到隔壁住,这间房子成了我结婚的婚房,一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我和夫人说,我们的婚姻之所以这么坚固,恐怕与这个牢房有关吧,“牢不可破”!
我的童年生活和“热闹”的批斗会息息相关。记着批斗资本家时,人都散了,资本家仍站在我们院大门洞的台阶上,嘟囔着“我叫赵小泉,我是资本家,我家三代剥削,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这种场合看多了,也就不害怕了。有一次,我注意到有一个围观的小男孩端着饭远远地站着,不敢靠前,别的小孩都走了,他还站在那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赵小泉的儿子。顿时,看热闹的心情变成恻隐之心。赵小泉仍在那儿念他的认罪词,我和赵小泉的儿子说,批斗会开完了,快领你爸爸回家吃饭吧。因为他家离我们不远,后来有几年我们俩也成了玩伴。
三、我的五个“发小”
重点说说我的五个发小。第一个是刘玉环,是我的小学同学,小名叫“环儿”;第二个是刘玉华,比我小一岁,小名叫“华儿”;第三个是顾修贵,小名叫“大里”,比我大一岁;第四个是马文彦,小名叫“小会儿”,比我小一岁;第五个是沙宏伟,比我小四岁,小名叫“宏伟”。他们每次与我见面也总是叫我的小名——“建禄”。
说说我小时候的丑事。总结来说,我小时候成熟较晚,有三大缺点:一是爱流鼻涕;二是穿鞋总把左右脚穿反;三是不爱学习。我至今仍然不解,我小时候为什么总是认为反穿的鞋是对的,这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心理结构问题?现在我年龄大了,到处受人尊敬。和发小在一起回忆往事时,他们说我的丑事,我就笑嘻嘻地听着,一点也不觉得不舒服。
说到发小,就要说说我的小学。我小学不爱学习,不爱写字,导致父亲天天逼着我写大字,但我都让发小帮我写,他们是我欺骗家人的主要帮手。据沙宏伟回忆,我在少年时期属于人狠话少的角色。他说,小时侯,自已的作业都不想写,更何况是帮我写。她也曾反抗,想溜走。我说,回来,不许走,一把拉他回来,然后双手按着她的肩膀座在椅子上,指着书说,从这里写到这里,写不完不许走。在我的震慑下,他不由分辨的,很委曲的帮我完成了作业。
我和大里
我和大里,还有华儿三个小孩,喜欢到处惹是生非,经常把别人家的水壶弄撒,花盆弄倒,让人追着跑。因为当时到处是大批判,小孩子没人管,所以几乎每天都要跑出几里之外去闯祸,家里人很为我担心。记得有一年夏天,有人在大街上乘凉,我和小伙伴就把西瓜皮扣在了一个人头上,之后就马上逃跑。
我和二楼的宏伟、小会儿玩耍时,已经长大一点了,经常给他们讲故事、算命、看手相。记得当时他们让我算命,我就说他们最近犯了小人,故意把事情说得很严重,把他们吓得要命。现在想来这些都是利用人的心理在做分析。当时他们也经常把他们的同学都找来,让我给大家算命,也看出我从小就有做咨询的天赋。
看了我写的《我的西镇“发小”》初稿,宏伟和远嫁到美国的小会儿聊了大半宿。宏伟后来给我写来一篇很长的补充意见,说我和同学们玩得很好,同学到我家不但帮忙干活,还能摆平一些事情。宏伟初二时受到隔壁里院的小男孩地狂追,他将此事告诉我后,我找了个同学一起去吓唬了一下这个小孩,从此,宏伟再也没有受到这个人的骚扰。他用了“罩着”这个词说这件事。我听得很有意思,像是在说别人。后来又一想,如果文革不结束,我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次聚会,王大娘的小儿子王世法和他的二姐王玉珍都来了。小的时候,我们都羡慕在山大医院当护士的王玉珍,我和大里当年跑到山大医院,藏在以为大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叫她的小名:“小恩儿,小恩儿……”。她回家后把我们的恶作剧告诉了王大娘。王大娘找到我们的家长,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回忆发小的故事,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原来我的情商从小就较高,发小是我生命中最早一个团队,在我的生命中是由一个个有生命力的团队组成的。1993年,我创办了长城所,后来能够成功,原来有生命之初的密码,由此,我也进一步认为经营好自己的团队永远是走向成功的重要一步。
四、我曾想成为诗人
我的发小故事经过幼儿、小学、初中、高中一直都没间断。顾修贵竟然找出了我的两首小诗,其中一首是我在酿造二厂当工人时候写的。
初春望海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日,晴
登亭望海心肺开,凉风阵阵扑面来。
阴雨之后阳光洒,满目碧波放异彩。
大好春光望不尽,风景秀丽醉心怀。
依山傍水思征途,激情满怀把笔抬。
艳遇
酿造二厂 王德禄
小小蜜蜂跑得欢,就是无处把脚站。
不是无花不采蜜。花多不知哪朵鲜。
看到这两首小诗唤起了我很多回忆,我十分肯定这两首诗是我写的。我的发小故事从流鼻涕开始,到发展成为一个圈内的诗人,这其中除了发小,我还和同学、朋友广泛来往,形成了很多个社交圈。其中,我认为写诗的社交圈与我的发小是没有交集的,但是发小们却不这样认为。
聚会的时候,发小们回忆说,当年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教大家朗诵过贺敬之的长篇抒情诗《西去列车的窗口》,他们现在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这让我很吃惊。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象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的确,我的青岛,我的西镇,我的童年,我的发小,那些难忘的岁月正“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
Recommend
About Joyk
Aggregate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ks.
Joyk means Joy of geeK